《我控诉》剧情介绍
《我控诉》长篇影评
1 ) 寻找自己的左拉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2 ) 《我控诉》:不沉默的大多数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
3 ) 匠心之片, 但有遗憾。
5星,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已历史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功过是非已经盖棺定论。
仅拿这部电影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影片里无处不体现着拍摄精致的质感,人物场景精心的考究,透露着艺术气息的匠心。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观感极佳,并带着一股70年代胶片电影的古典风。
至于人物,只能说殊途同归,都是想维护国家的正义,军队的荣耀。
有的人想排除异己,遮羞蒙弊。
主角则想伸张正义,公正对待。
但还是保留了个人看法。
我能同时理解双方的做法与出发点,只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结局也不可能完美。
即使才华横溢如本片导演的人,也无法掩盖污点,这就是人生。
4 ) 2020年2个国家2部政治历史片
我控诉和七君子,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
时隔七十年左右,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
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应时应景。
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国家,军队,重权,人民,个体。
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
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
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
5 ) 他并没有底气为自己控诉,但电影无罪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
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
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
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
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
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
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
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
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
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
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
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
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
罗曼·波兰斯基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
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
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
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
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
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
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
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
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
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
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
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
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
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
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
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
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
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
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
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
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
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
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
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
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
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
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
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
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6 ) 不老神鸡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7 ) 辩证看待历史唯心主义电影《我控诉》——为意识形态服务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
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
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
),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
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
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
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
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
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
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
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
8 ) 冤案终将昭雪!良知终将战胜谎言!
放硬盘里几年了都没舍得看,毕竟罗曼波兰斯基已经那么老了。
拍一部少一部。
今天终于给看了,毫无疑问的满分。
摄影,构图,服化道,化妆(包括符合时代气息的胡须与发型),对白,演员的表演,选角。
剧情的推进和叙述,分镜,叙事节奏。
反正恕我愚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而且也很欣赏和喜欢。
只是法语总是听着不如英语习惯和舒坦,虽然英语我也听不懂,啃不了生肉,但实在看多听多习惯了。
里面颇几句金句对白。
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上校和情人告别前说,说不定自己会也关去魔鬼岛,上尉会高兴自己去作伴时,噗嗤笑出声来,幽默呀!
冤案!
冤案!
冤案!
果然全世界绝大多数腐朽没落的官僚系统都一样,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掩盖最初的谎言,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并揭露真相!
当上校在办公室对诡辩的胖少校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
当上校对上尉的弟弟说,不要谢我,我只是遵从我的良知时,真的是要拍案叫绝!
9 ) 《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有关徳雷弗斯案件的描写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
10 ) J’ACCUSE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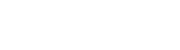



































































抛开波兰斯基米兔那点事儿,我还是单纯地想看看《我控诉》的,毕竟动静这么大,好奇也该看看。然而不只云里雾里地撑了半小时后,我放弃了,算了,2倍速我都嫌慢。现在我也是个没耐心的人了,忍不了一个老掉牙的导演跟我磨磨唧唧不知所云地讲故事了。越是名导你越这样拍片我就越想骂你。真不如去看看吕克·贝松的荷尔蒙爆浆刺激小烂片来得开心自在。Lucy的特异功能不好看么?Anna的超模大长腿不好看么?为什么要看一部老头子的片子来催眠?况且我现在也不失眠了。你控诉,老子还控诉呢。
损失八年的名誉与时间军衔已然无法偿还,真正流放在恶魔岛的是政治迫害。坚持鸣冤的人会被高墙阻隔,坚持真相的人会被发配边境,坚持发声的人会被冷枪击倒。这封拼贴的情报可以控诉任意罪名,这信件上的字迹可以嫁祸任何无辜。当年在学校发誓不会对犹太人有任何偏见,竟然用了十二年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片头提示“全部真实历史人物”,迎面真诚。荣军院一幕简直完美复刻当年的报道画面。将一件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缜密还原,不仅是匠心还有勇气。波兰斯基的美学太舒适了。从二审到无罪全部省略,可能出于篇幅考虑,有点可惜,后半部分的节奏匆匆有些未完成感。又是一个犹太共情式的结尾,比起赞美白人英雄主角,更重要是提醒反犹主义阴影仍笼罩着:他们的八年不同。德雷福斯的孙女将与波兰斯基的母亲将共丧奥斯维辛。悲剧命运似乎冥冥写就,苦难才刚刚开始。不忘初心的作者。
三个字:稳!准!狠!节奏把控尤其得当。
三星半就标三星吧,毕竟已经很多五星护体。片名叫我控诉其实视角在调查者,等于抽离了当事人情感。调查者毫无人性瑕疵最多和别人老婆搞一搞,当然导演也不会觉得这算问题。导演水平确实高明显得不露痕迹,但是和自己相比也没有太多亮点。
“虽然有点搞笑,但你要服从”
波兰斯基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阴沉简练利索,他的电影很少在台词出现金句,因为波兰斯基太会用电影画面讲故事了,台词基本就是陈述剧情用的,而推动剧情发展和冲突全放在镜头语言上,这才是电影最注重的影调呀。对于电影,罗曼波兰斯基是天才。
因为颁奖礼上她们退场,只好对该片不置可否。艾玛纽尔·塞尼耶 ,唉,女绳的蜕化还是退化?
四平八稳,没甚惊喜。
真他妈闷
一篇"我控诉"掷地有声 于历史 也于自己;没想到德雷福斯事件还间接催生了环法自行车赛
单就电影本身来说,过于平淡,以至可以用平庸来形容,除去古典的色调、克制的镜头,实在别无可夸。而电影主题,是否适合交由波兰斯基拍摄也相当有争议,当了解影片主题的时代背景、事发经过结果后,会觉得“我控诉”和“波兰斯基”印在一起本就充满了荒诞感。
可以说对我这种脸盲非常不友好了 里面所有的男性都穿着几乎相同的军装 留着同样的胡子 名字还是一大串 看到一半我就懵了 再者 我对这种美其名曰克制 实则就是无聊的历史电影毫无兴趣 要不是因为凯撒电影节因为这片子闹得沸沸扬扬 我肯定不会来看这一部 我只看过波兰斯基的两部影片《钢琴家》和《穿裘皮的维纳斯》都不喜欢 加上这部 波兰斯基可能成为我最讨厌的“世界名导”了 (好像性侵女童就足够令人讨厌的了)
波兰斯基真是稳到不行,转场干净,镜头语言冷静克制,又时刻调动着观众情绪。可惜现如今他作品的光彩总是会被个人私事带来的争议所遮蔽,实在太遗憾了。好久没看Vincent Perez了~
上帝太多。人类太少。
对于如此错综复杂且影响力巨大的德雷福斯案件,波兰斯基选择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切入点,这就证明了这部影片的目的,并不单纯像很多人事先揣测的那样是在借影片为自己辩解、诉自己的冤情。皮卡尔确实在为德雷福斯的清白努力奋战,但整个过程呈现得非常冷酷克制,没有为了正义挑灯夜战的蒙太奇,没有此类型常有的煽情戏码,两个角色仅有的两场对手戏透露出的是“公事公办”态度。这些去英雄主义的冷静处理,证明了《我控诉》更为宏大的主题,是指向这个“公”,这个藏污纳垢互相包庇的系统。皮卡尔不是什么正义使者,而是一位称职螺丝钉,他代替狱中的德雷福斯,带我们重走了一次布满陷阱的审判之路。/“我控诉”的排比段落拍得力道十足,每一段都是一个近景拉一个远景,被控诉者念出他们的罪状。
0分和满分都是矫揉造作
我看到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法治,军人和贵族的荣耀,从内部质疑的勇气,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敢说真话的报纸……铁幕两边,一边把德雷福斯写进历史,一边把千万个德雷福斯直接抹去。法国人素来以狂热闻名,但如果狂热会犯错,那也不是自由的错。“劣迹艺人”波兰斯基再遭抗议,至少还能拍电影不是吗?
(本來看了2/3昏昏暈睡想說波蘭斯基把這麼可拍的Dreyfus affair拍的這麼老掉牙真的大可不必,然後左拉就出來了!!)每個時代都有人為greater goods辯護,西方文明的公理卻應該是:個人或真相不應該為了假設的集體利益而犧牲。實際上,這些犧牲品非常普遍。就greater goods作為閉嘴費來說,這是個體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抵抗集體本能生活的結果。這片十有八九也是波蘭斯基對metoo的回應。電影中主角一方敗訴後和胖子henry的比武簡直神來之筆,姜還是老的辣。
可以说平缓又沉稳,也可以说是很沉闷了。一些镜头还是不错的,配乐也行,只是难以拉回昏昏欲睡的我。巴黎一百多年前的样貌,还原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