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剧情介绍
音乐人阿鲁斯(伊德尔 饰)因不满哥哥对患有阿茨海默症的母亲(巴德玛 饰)的照顾方式,决心带她返回草原,去寻找母亲记忆中的家。为了防止母亲走失,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似脐带一般的连接,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逆位”母子情,牵引着两人向草原深处漫游。当爱由彼此羁绊化为理解和自由, 母亲终于回到心中的故乡,阿鲁斯也得到平静和爱的力量。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全美洗车女郎听爸爸的话!播种的旅人传说的故乡驱魔大师天使的心跳特别篇:地狱厨房你杀死的东西艾伦·德杰尼勒斯:请你许可蜡笔小新:我的搬家物语仙人掌大袭击隋唐英雄3特殊嫌疑犯漠北七雄:狼王摔跤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虎胆神鹰厨神小当家第二季机智医生生活疯狂熊孩子祝你好运勇者之战冥冥之中驭影师幸运怪兽嘻哈四重奏第五季三个家庭七人乐队失形鸡犬不宁五岛医生诊疗所最终频率千方百计回归
《脐带》长篇影评
1 ) 电影只有拍完,才能见证成长——专访《脐带》导演乔思雪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
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
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
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
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
可是“家”是哪里?
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
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
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导演乔思雪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
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
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
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
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
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
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
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
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
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
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
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
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
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
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
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
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
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
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
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
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
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
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
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
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
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
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
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
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
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
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
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
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
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
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
什么是传承?
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
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
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
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
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
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
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
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
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
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
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
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
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
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
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
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
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
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
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
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
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
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
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
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
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
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
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
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
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
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
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
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监制曹郁、姚晨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
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
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
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
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
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
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
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
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
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
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
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
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
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
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
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
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
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
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2 ) [觀影分享]|臍帶
電影院「包場」觀影系列——《臍帶》導演:喬思雪01. 觀影後感🎬在電影院裡看的。
排片非常少而有排片的影院也都坐落於偏遠的郊區,再加上是工作日,所以我看的這場全程只有我一個人。
畫面與音樂都非常震撼。
電影選用了很多大遠景、拉鏡頭,擴大了草原在銀幕上的空間感。
而電影裡以女性為主、敬畏自然的鄂溫克民族、壯麗遼闊的草原和(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蒙語,都成功地把我代入進了那種粗獷純真的原始自然裡。
(P.S. 導演本人便是出生成長在草原的鄂溫克族人)02. 以下是「涉及劇情透露」的影評📽Spoiler alert 🚨 弟弟「阿魯斯」因為不滿哥哥對老年痴呆母親的照顧,因而把母親帶回了以前他們在草原居住的地方。
又因為母親生病經常到處亂跑,所以選擇用繩子把母親捆住,以防她受傷走丟。
這是片名的來源,繩子象徵著「臍帶」,連接著母親與孩子,同時也是“孩子”和“母親”之間糾葛關係的外化。
繩子的一頭栓著一個女性的母親身份,另一頭拴著男主身為孩子的安全感。
當我們的社會不斷地在強化女性作為「母親」的身份角色時,好像一個女性一旦成為了母親,她便從那刻開始,一輩子都得是一個「母親」了。
所以阿魯斯一開始無法理解已患老年痴呆的母親想要回家的行為。
他無法想像這個他視作「母親」的女人要離開他,要回她「自己的家」。
孩子遺忘了「母親」在成為自己的母親之前,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個體,擁有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有獨屬於自己的童年與青春記憶。
而電影裡那棵半生半死樹,似乎也象徵著母親的狀態變化。
枯死的部分象徵著「母親」的身份,照應著現實里媽媽的逐漸老去;茂盛的部分象徵著「女兒」的身份。
母親作為「女兒」的記憶逐漸鮮活,而在現實里,母親的行為因為生病變得像小孩子一樣,某種程度上的「返老還童」。
(其實仔細看電影裡還有很多象徵著電影標題「臍帶」的景觀,例如河流、大路…)而當阿魯斯帶著母親不按照「路」開車時,我想他便已經逐漸坦然地接受母親的離去了。
從一開始只要母親安全不受傷,到最後放開母親讓她去尋找她自己的家,“孩子”也獨自完成了剪斷「臍帶」(與母親的連結)的過程。
(&. 個人最喜歡的鏡頭是母親的幻覺部分和最後母親的離去。
兩處鏡頭移動非常驚艷。
從開始的方塊窗戶到最後的藍色塑料洞,有一種時空穿越感。
透過藍色的塑料窗,母親看到了一個跳舞的女人和爸爸媽媽(跳舞的女人應該是薩滿)。
母親的爸爸媽媽站在那裡,好像一直在等待「母親」回家。
)
3 ) 有一天月亮落下的时候,我来接你回家
这两年开始面对父母的断崖式衰老。
不是那种白发、皱纹的老,是要每天盯着他们吃药,经常去医院、偶尔做手术、住院、陪床,和不遵医嘱的他们斗智斗勇,以及陪伴他们度过漫长治疗的老。
很奇怪,在这之前,他们在我潜意识里一直是三四岁的模样,整天忙忙碌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偶尔吵架,就会拿出长辈身份讲些颐指气使的话,我自然不听,只想着怎么快点长大,能真正独立到逃离他们。
也许正因为真正逃离过吧,40岁以后的父母在我记忆里几乎是空白的,直到这些年再次走进他们的生活,才发现他们居然已经老成了这个样子。
昨天送倔老头儿去医院做常规治疗,他非让我先走,说陪在那儿一下午没意义,他不想麻烦任何人包括我。
我拗不过,只好把带的水塞到他手里说:医生说多喝水,你要听话啊,别一下午都渴着。
看他拿着小水瓶过马路的样子,忽然觉得自己很像是送他去上幼儿园的妈妈。
电影里第一次让我没忍住哭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段。
阿尔兹海默的妈妈发现自己尿床了,害怕被看到就想要用被子盖住,儿子赶快跑过来抱住她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尿床,太阳一晒就什么都没有了,没事啊。
”妈妈听完愣了一下,紧接着把头靠在他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说:“爸,你终于回来了”是的,曾经妈妈也是女儿,是她父母的宝贝。
后来她长大了,成了妻子,成了母亲,用自己的一部分换取了家庭的稳定、孩子的成长。
多年后她老了,这时身份对换,某种程度上妈妈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家长,他们又回归到需要手牵手才能走下去的关系,一直这样到路的尽头,那时连在他们身上的脐带由孩子亲手剪断。
他放她回到她的父母身边,从此再没人把他跟死亡隔开,他的人生来处已逝,只剩归途。
电影跟《我的阿勒泰》一样好看,拍得像诗歌,像散文,像民谣,也像一个传说。
音乐、摄影、巴德玛的演技都在不停的疯狂输出,想着不哭不哭干啥啊只是看个电影啊…最后还是哭得一塌糊涂[哭惹R]一下就懂郭采洁为什么要跟伊德尔结婚了,管他呢,就是这一秒,爱了再说吧~(全平台同名:杨素瑶。
原创不易转载小窗~感谢关注)
4 ) 草原城市和阴阳树
生命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保护,是尊重其选择。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物形象/弟弟阿鲁斯:从自以为保护母亲到认识母亲最后成全母亲。
母亲娜仁佐格:在墙上画着蒙古草原(向往着自由不想被束缚);面对儿子们争斗“你们哪有儿子样,哪有兄弟样”好似站在客观的视点对兄弟二人评价,又好像回光返照一般清醒;阿鲁斯在树林里找到的那只牛就好像他的母亲一般茫然无助;看到车就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车就是通往家的工具,只要上车就能回家。
哥哥:顽固的守护着母亲。
女人:阿鲁斯母亲一般的存在,帮助他鼓励他仰慕他爱恋他。
不同于女性,男性对待家庭的意识更像是一种保护和情感上的占有。
从大男子主义出发,以保护为由,让失去行动能力的亲属听从自己的所谓的最好的安排。
但是却不考虑亲属的感受,只做着自己最以为正确的的决定。
影片最后,具有宗教仪式一般的母亲的父母以及他们带来的随行队伍叫魂一般喊走了娜仁佐格,儿子不同于以往的保护主义而是采取了自由主义,割断了那如脐带一般链接自己和母亲的绳子。
在蒙古人眼中,死亡和新生一样重要,母亲割断脐带,儿子诞生,儿子割断如脐带一般的绳子,母亲离去,两者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意义。
现代事物的侵入:传统马头琴和现代电子琴、交通工具马和汽车、马靴和运动鞋、无人机劝退。
影片在表现母与子之间的关系之时,也用了一些笔墨描写这些现代事物对于他们本来生活的冲击,致使其茫然的一种社会困境。
对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母亲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儿子也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一步一步重新接洽传统事物,放弃传统观念,尊重母亲的人格,让其自己选择生命的路。
脐带:母亲和弟弟之间的那条绳子蜿蜒的河和湖(脐带和胎盘);路;在草原上的房子(如同胎盘孕育新生儿一般保护着他们,直到被撞坏,意味着闯入者的侵入)和塑料布(胎膜一般)。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影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起到链接作用的事物,他们都是脐带,链接着母亲和儿子、链接着现代和传统、链接着当下和未来。
5 ) 《脐带》:断开的脐带,是与母亲最后的道别
脐带对于婴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它在母体内,成为供养婴儿生长的生命线。
但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脐带需要被剪断,用割裂与母体的自然纽带的方式,来到人间,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真正实现用口鼻呼吸,体验这个世界带给柔软的肺部最初的呼吸的疼痛。
影片取名为《脐带》,从具象上看,是连接母子之间那一条长长的绳子,从情感上看,是一直牵绊的母子之情。
母亲因患病“变成了小孩子”,于是乎,需要儿子以大人的方式来照料,此时,这份羁绊彻底逆转。
母亲不再是母亲,母亲变得自我、变得自由、甚至变得陌生,但她似乎回归到一个最初的我。
她不再是母亲的身份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只是那个喜欢音乐、喜欢跳舞、喜欢小羊、想找爸爸妈妈、想回家的一个小姑娘。
影片着重描绘了母子之间的情感,陪伴是儿子能为母亲做的最棒的事。
从一开始的限制母亲的自由,到带着母亲去寻找生死树,两个人一路前行,在内蒙古大草原之上肆意驰骋,在敖包边翩翩起舞,在火堆旁久久凝视。
这是送母亲回家的路,这是一路道别的送别之旅。
最后的最后,儿子拿出刀切段了两个人之间的绳子,犹如当初他自己出生时被切断了脐带一般。
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真的要离开了母亲,这一次,他的肺没有疼痛,他的心在痛。
曾经的脐带之断是为了相聚,这次的脐带之断是为了离别。
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歌手或音乐制作人,在他的生命里,音乐占了很大的比重。
当母亲变为小孩子时,我们发现她也是如此喜欢音乐,或许这份传承就来自这里吧。
蒙古族人热爱唱歌,喜欢跳舞,在苍茫大地上,处处皆音乐,他们的乐感和动感是那样自然,与生俱来。
影片整体都有一种音律在流淌,蒙古族的歌曲配上草原的辽阔苍茫,让人感觉无比孤寂又无比充实。
音乐,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音乐也从镜头中流淌出来,蔓延到你我身上。
影片的电影语言是极棒的,充满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民族风情。
镜头语言简单明了,没有故意炫技,相反,是一种诗意的叙事方式,展现出草原上的脉脉风情。
草原儿女的情感,真挚且热烈,细腻且张扬。
无论是大场景的航拍,还是小空间内的情感表达,都很质朴,很动人。
特别是影片中有几场如梦如幻的梦境戏份,带着一种神秘色彩,非常引人入胜。
这里的镜头语言的展现方式,如行云流水一般,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影片整体呈现出一种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是一种带着诗意和浪漫的色彩,高于生活本身,却让人相信这份存在。
画面在色彩呈现上添加了很多蓝绿色,给人一种复古的感觉。
夜晚的场景里,火把、篝火、电筒、月亮的光芒,那么真实又如此梦幻,仿佛油画一般,仿佛进入了一场梦境。
这部影片让我感觉很舒适,它呈现出一种情感的美,一种离别的美,一种诗意的有节奏和韵律的美,让我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动。
2023年3月18日 星期六 21:32
6 ) 家到底在哪里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
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
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
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
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
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7 ) 歌单
《AYARN》作词/作曲:伊德尔《SER》作词/作曲: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ZALUNAS》作曲:欧尼尔《ALTAN ALTAN JIGJUUHAI》鄂尔多斯民歌 演唱: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ZANDAN HURENG》鄂尔多斯民歌 演唱: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巴尔虎摇篮曲》蒙古族巴尔虎民歌 演唱:卓拉《SHIRDEGIIN CHAIDAM》作词/作曲/演唱: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走马》蒙古国背勒格舞曲 演奏:欧尼尔《吉尔拉》俄罗斯民歌 作词/演唱:欧尼尔《UNDUR UUL》鄂尔多斯民歌 演唱: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太阳泉》(Naran bulag)布里亚特民歌 蒙古语作词/演奏:欧尼尔
8 ) 《脐带》之外
遥远的草原小镇,电影却是连接我和世界的生命之绳。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温克旗的小镇里,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每周末和父母看电影录像带度过周末,千禧年之后我开始自己租DVD看电影,北京奥运会之后网络下载电影资源永久替代了所有其他观影方式。
看电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体会生命中无法体会的情感,抵达无法抵达的世界,让我的视角不再集中在一件事情的正面,我学会站在侧面看它,绕道背后去看它。
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和世界对话的欲望。
我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游子,在世界的舞台上流浪。
或许是身体里的游牧基因在作怪,我的故事里总有人回到故乡,或是有人在地球的版图上游牧,但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蓝色圣洁的高地。
生命中的偶然和突如其来的告别给生命以启示,伴故事里的人不断前行。
拍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以及对与亲人告别的恐惧。
通过一个绳子将一对母子系在一起,探讨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探讨与故乡的关系,以及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
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临和亲人告别,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支撑我们面对离别和死亡。
我想我出生长大的这片草原给了我答案,就像片尾母亲的那句“时间会一直不断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一直盛开”生命有来有往,我们要接受万物的无常,以及生命在自然里有轮回。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离开草原到城市学习生活,我们把烙印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带了出去,怎么让这份文化在城市里生根发芽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探索的,还有一些人从城市返回草原,把城市里的现代化文明带回到草原,怎么让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下去也是变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
其实伊德尔我在写这个剧本之前就认识他了,他做音乐的理念给我很大启示,他从小学习马头琴,到了北京他在探索怎么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他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大众最能接受的传播方式做他的音乐,这跟我想拍这部电影很像,用我们年轻的视角,年轻人的方式记录时间,讲一个最质朴的故事,传播来自自然的信仰。
所以出走和回归不是对立的,像死亡和新生一样,就像片尾的那棵阴阳树一样,在盛夏的时候,枯萎的那棵树将它的营养传送给枝繁叶茂的那一棵树,让它长出新的形态,向阳而生,就像我们的当代文明建立在传统文明之上一样,以自己新的样貌不断繁衍生息。
蓝色的蒙古高原,心中的高地,你把我们凝结在一起。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一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把来自故乡的味道和草原的哲思用拍电影的方式保存在时间里。
很多人会说作为导演乔思雪很幸运,处女作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确实作为一个处女作导演来说,能和这么业内顶级的主创合作,确实是一个小的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也很难在未来复制。
作为《脐带》的监制曹郁先生和姚晨女士,为《脐带》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和支持,从剧本到这个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视频通话讨论剧本几个小时,把它打磨成一个真正可以接受考验的拍摄脚本。
拍摄期间监制曹郁老师除了白天要完成摄影师的创作,晚上还要和把控后面的拍摄计划,拍摄尾声曹老师经历家人离世,忍受巨大的悲痛和压力再次回到剧组陪我们拍完最后的两场戏。
最初在姚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为演员定下表演基调,作为表演指导老师的她还要负责帮助那些没有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进入角色,让他们真能在电影里活起来。
作为监制的他们,付出的远比监制这个工作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热情。
在这个独特的拍摄体验程里面,他们不断地帮我认识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帮助我建立在片场的自信,直到这部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还在四处为《脐带》而四处奔走,只为这部真诚的作品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
《脐带》的出品人制片人刘辉,最初在first电影节创投挖掘了这个故事,并全程陪伴《脐带》走到了最后。
两位制片人刘辉、胡婧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未表现过丝毫的退缩,给了我心理上极大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坚持下去把这部片子做完。
更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找到了我们的声音指导富康,美术指导赵紫冉,造型指导李宙,这些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主创班底,给了《脐带》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最早进组的美术指导赵紫冉,往返于冰天雪地的森林和城市间,亲手打造了那个如梦似幻如同子宫一般的老房子。
造型指导李宙,跑遍了呼伦贝尔的民族服饰店、牧民家只为找到那些有生活痕迹的蒙古袍。
执行制片人姜乐从自己的仓库里拉来的帐篷桌椅板凳,在篝火那场戏因我们用完了六吨的木材,没有可烧的材料,把他带来的桌子椅子都扔进了火堆,只为让我们能再多拍几个镜头。
这部电影里我们的两位主演,巴德玛老师和伊德尔从最初的陌生人,慢慢的相处成了真正的母子。
巴德玛老师身上所带有的轻盈、纯真、质朴的气质,让母亲不再是剧本里角色,而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草原母亲。
伊德尔奉献了他所有对生命和音乐的感受,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阿鲁斯这个角色。
还有那么多普通的素人演员,他们构建了这个电影最真实质朴的瞬间。
剪辑指导张一凡,将脐带的剪辑风格调整到了一个最靠近观众,又最大程度保留创作者意图的版本。
声音指导富康,在声音后期制作中,根据他的真实情感体验手动推音轨,把空旷的草原填满了属于人物内心的声音。
调色师张亘,将如此丰富细腻的色彩带给观众。
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三位音乐人的音乐作为一条隐形的脐带,将这部片子里母与子的情感纽带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这部片子的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自于呼伦贝尔当地,他们带着对电影最赤诚的爱和热情,帮助我们拍完了这部有独特风味的草原电影。
《脐带》有种神奇的力量,将所有喜爱这个故事的人凝结在一起,帮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剧本到今天走进电影院,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借助光影、声音、音乐的力量礼赞生命与爱。
9 ) 《脐带》诞生记—专访制片人:刘辉、胡婧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
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
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
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
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
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
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
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
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
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
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
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
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
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
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
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
《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
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
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
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
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
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
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
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
《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
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
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
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
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
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
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
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
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
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
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
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
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
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
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
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
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
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
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
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
《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
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
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
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
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
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
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
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
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
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
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
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
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
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
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
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
《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
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
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
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
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
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
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
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
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
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
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
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
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
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
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
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
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
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
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
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
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
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
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
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
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
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
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
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
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
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
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
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
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
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
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
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
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
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
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
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
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
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
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
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
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
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
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
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
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10 ) 什么时候回家?
小的时候没有电话,出去之前爸妈总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答案就一个,玩一会就回了,但是每次都玩的很久。
长大了,总是以工作忙,有点累,想睡觉为借口不去看他俩。
但是心里不慌不忙,因为我知道,家就在那里,无论玩的多久,无论多久没去蹭饭,他们一定在家里呢。
电影讲的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阿妈想要回家,抛下所有,变回最初的样子,去找她的家人,她的阿爸阿妈了。
很感人,景色很美,看的让人流眼泪。
这几天得去看看我家的老两口了,想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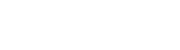



















































优缺点都很突出的电影。视听水准相当拔群,曹郁的摄影、当代新潮化的蒙古民乐,都是那种眼睛和耳朵“可识别”的高规格质感。巴德玛老师的演技,伊德尔的个人魅力,也是非常大的加分项。在林林总总的硬软件维系下,整体影调气质是稳定统一的,这对新导演来说蛮难得的。但就是剧本和表达的平庸…很难评,就不评了吧。
#4thHIIFF# 故事讲得不算特别顺滑,设定有点硬,后面又有点草原风光mv了,但胜在情感真挚,所以观感不算特别差。脐带/绳子的意象不错,脐带是羁绊,绳子是束缚,而这正是亲人的两面性。但看到最后,觉得多少还是有点过于依赖这个意象了。整体的话,一星给曹郁老师的摄影,加持很大;一星给音乐跟草原风光,该说不说,确实美;还有一星给巴德玛老师的表演,不给影后真的会生气!
非常喜欢窗外幻觉那一幕:篝火明亮,红裙飞扬,有人在呼唤你少女时期的名字,草原无比广袤,而故乡渺远,河流、土路都是脐带,两端系着归人与游子。
乌仁娜是我最喜欢的蒙古族女歌手,湖边音乐响起的一刻,实在有给五颗星的冲动。
脐带既是纽带也是束缚,第一次剪断是独立,第二次剪断是放你自由
同行记者:看了半小时后长睡不醒
摄影精致+声音设计精致≠视听好,包裹在风景里的只是很常规的亲情公路片,而电影对阿茨海默症的呈现就只能扶额了……糟糕的地方有点像那部《白云之上》。
看到了篝火纷飞、明月点亮湖面、众人起舞的场景,那一刻我倍受震撼,眼泪似乎是为了想要记下此刻的文化图景,感受到导演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切断绳子的意象,总觉得不只是切断脐带这么简单,或许也在表达切断血缘、切断自私的眷恋。“生命的轮回”通过每一个细节传递得非常准确,创作者回答了自己关于生命的追问。最惊喜的是细节处理的都不土,洋气,很多极其容易变矫情的情感戏都用幽默/高级的方式处理了,母子戏的处理值得学习。音乐也可爱。儿子:“她会永远爱我,只是她不记得了。”母亲:“没事,时间会一直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常青。” 什么神仙回答,极其具有牧人的特色,不含任何“牺牲、pua意味”的爱,对母亲最好的放手也许就是放她回到她的来处,这是草原的答案。
草原生活的细节很好,音乐也好听。但是阿尔茨海默症哪有这么乖啊,美化得太过了。喜欢姑娘说的“喜欢你做音乐,这里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也不是一直生活在过去。”
在城市里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却不得不打着民族文化的口号来得到一些关注和机会。用着自己极具刻板印象的回忆拍一个属于民族“猎奇”故事,用新鲜的话语讲述着传统的价值观,用先进的技术重拍那些烂俗的隐喻,再配上即传统又现代的配乐。脐带这个象征成了说服投资人的直白工具,最后再加上点社会热点,一个成功的文艺片模板。以为能看到草原游牧民族的价值观,结果只收获了漂亮的风光。(两个旋转镜头真的太过于做作了。。。)
这么牛逼的电影是怎么被拍出来的电影圈有这么多说实话的人这真是电影最好的时代 牛逼 牛逼 牛逼 电影圈都是牛逼的人
超乎预期的电影!@ 成都鹅影
少数民族电影,无论拍的好不好,那种真挚的情感和豁达的心态,就很动人,很喜欢电影名,不仅是母亲对子的纽带,也是孩子对母亲的依赖,电影后面太像美丽的风景mv了🥺
1.上个月和励志姐通话,她说她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我就问她为什么会期待《脐带》?她笑着说这个问法蛮有意思的,我回她,我就是因为片名叫 qí dài 所以才用了 qī dài 这个词;2.饰演男主角阿鲁斯的伊德尔真就是与郭采洁合作的那个音乐人呀;3.有些质感不错的影视作品少人问津,有些粗制滥造的视频播放量高,现实的现状;……
1.前面不错,到中间最出彩的就是带摄像头的无人机催人离开私人草场,到最后篝火歌舞的时候就像是参加旅游团的篝火晚会了,片子在这里彻底垮掉。2.脐带的隐喻很清晰也很好理解,具有迷惑性的是母亲的隐喻并且是生病的母亲。这个设定带来的感情上的认同和代入让人更容易被迷惑。3.母亲生病了,在外的孩子回来吧,既可以照顾母亲也不耽误事业,还有漂亮善良温柔的姑娘奉送。说穿了,顺滑的寻根,就是不断的往后退的保守主义,背后的观念非常陈腐。
勇气之作。题材本身是极具普世情感的也是最能引人共鸣的,但在表达方式上选择了非常沉稳的,文艺的,安静的,比较远离市场的方式。电影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用nb的摄影圆润的声音设计了一场温和又汹涌的视觉盛宴。技术层面能聚齐这种业界大佬,出品方也真的是用心了。
蒙友虽然不齿总拿民族身份文化说事,但这片还是尽可能朝着万马方向和人类情感共通议题去深入了的。也有台词“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时间总是向前走的”嘛。而且情感和形式表达都很美。
中途一度很迷茫,以为想讲个人梦想和家庭的取舍,家乡和城市的选择,但都没提到。还以为会往公路片的方向走,结果也没到目的地。到了篝火旁,才发觉影片也没有想去哪里,角色也没有纠结什么,只是想陪陪妈妈了。“时间是不断向前的,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长青。”
开头的歌感觉还挺好听的。
2023.3.26点映,很平淡、很亲情的寻根公路片,随着时间的流逝,“脐带”两端的母子何尝不是一次身份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