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蜘蛛》剧情介绍
一张新公寓的平面图,两天的搬家进出,莉莎即将告别与玛拉同住的日子,所有的亲密与角力、回忆与张望,都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幽微地拉扯著。各方好友、家人、工人、邻居或小狗逐一现身,通通汇集到搬家现场,但每一次的错身或交谈,都有着不寻常的气息及欲望在狭缝里流动。有些家俱将被带走,有些记忆会被留下,莉莎、玛拉与这群好友之间的互动和情谊,都随着不时响起的华尔滋舞曲,在一进一退之间,谱写出充满焦虑、嫉妒、暧昧、孤独交织的浪漫小节。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拳影人生戒酒吧拜托了立花登青春备忘录黑夜吞噬世界策马狂奔失忆24小时衡山医院门徒最危险游戏第一季红男爵辛普森一家太棒了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一季:我和诗圣做搭子断毒所言所行干涉鲨滩蛇之道大内密探之姻缘劫最后的佣兵暗夜凶光爱情无线牵女高中生的虚度日常俩王四个2爸爸的小提琴#远程恋爱~普通的恋爱是邪道~笙秋塔拉德加之夜39度青春芝加哥警署第九季
《女孩和蜘蛛》长篇影评
1 ) 女孩和蜘蛛
怼着中景拍的方法把这个局促空间的限制给规避掉了,而局促空间又给了电影本身的寓意,只是一个两天一夜搬家的故事,也只是一个搬家故事而引发的女孩身边蛛网似复杂人物关系的梳理和情感的探索,因为时间短,所以蛛网无法拓展来写,过于多的长镜头则毫无意义,而恰恰时间短、中景怼脸拍把蛛网的定义结合的良好,再加上明亮的置景下不至于让局促的空间显得阴潮,只用女孩的眼神和情绪表达着她对她身边周遭人或物的喜厌和追溯。
但从影片本身的寓意而言,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深刻,更适合短片:)
2 ) 2021的惊喜礼物
用整个影片打造一个寓言,并用众多隐喻去填充,模糊背景动机,用情绪推动人物;我本是讨厌这种手法,但规模到这个程度,并用多种视听手法丰富可谓创新了,预定今年最惊喜。
蜘蛛(丝)正如人与人的关系,拓展、纠缠,互相伤害/爱慕,想要上前却处处掣肘,想要拥抱却一拳拍死,于是渐渐淡化、消失。
导演用凝视、走位、光线、三原色和固定镜头表现人物关系与情绪变化。
最典型就是: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衣服颜色(红黄蓝)表达不同的制衡关系。
比如黄色代表嫉妒(第三天的楼下女),那么它很可能同时和红色(第三天的搬家女)和蓝色(第三天的女主)产生对峙关系;又如搬家女母亲和装修大叔第一天同为蓝色(互有好感),第三天穿上白色就出现了罅隙(开始考虑女儿的不满),但套上蓝色假发那一刻依然开朗的;黑白两色多数时候是中立,但黑白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第三天的女主和男主)。
小道具的巧思不错,比如“渐渐丰富的房屋图纸”被“不断洒掉的红茶”侵染,正面与负面交织的隐喻。
我之所以说这是寓言,除了人物叙述的不明所以的小故事,还因为我想把这个公寓(搬出的公寓)看成“一个人的脑内性格的集合”:a、老奶奶是为爱付出且勇敢的(喂猫/雨中摇摆),是性格上限;b、楼下二女表现出嫉妒、激情、引诱,是性格下限(尤其夜女王,感觉是楼下女的潜意识一般);c、女主在中间,纠缠于搬家女/母亲、男主的关系。
女主的纠缠关系最多,但最少说话,有时甚至像个局外人,但心思都很明显;搬家女似乎是性格中的阴郁因子,缺乏耐心,迟钝冷漠,二者闹掰似乎是某种情感分离的展现,同时也有童年问题;男主是外来因素,不算性格内。
综上,是为表层性格;d、远去的渡轮是期待中的远方,女仆即是大家理想中的生活态度。
每个性格(每个人)都期待放下纠缠、按照自我意识行事;但暗下的光线、破碎照片代表了导演的悲观态度。
蛛网会继续纠缠,此消彼长。
或一方消耗殆尽、或旧事重燃。
3 ) 蛛网里蔓延,扩张和断裂,粘稠的嫉妒,欲望和爱
镜头和色调的轻盈好像专门用以抵消一整个基调和留白里的张力。
但是丝毫不觉得内部的轻盈和纯真,听到名字的一瞬间就觉得有一丝隐约的邪恶在里面。
搬家的两个女孩Lisa和不舍其搬走的Mara,俊秀却被困在整个人际关系的蛛网里,被女子的情欲而裹挟得身不由己的Jan。
可能是因为将空间和时间都压得很窄,觉得稀松平常的日常流逝里感官的敏感被调动到最大程度。
听觉,楼上传来孩子们蹦跳的脚步声,角落里孩子的哭声,夜半的风雨,蜘蛛簌簌的爬行。
视觉,静物的蒙太奇和笼罩在各种光影里的人的脸。
倾泻的咖啡,流泻的红酒,环环相扣的凝视里有恨有不舍有猜忌有情愫。
三原色的运用又有几分戈达尔《狂人皮埃罗》的感觉。
用色极其大胆,但是却不觉突兀。
或深或浅的背景光晕里色彩的凸显,包括有影迷认为其配色颇似候麦,但是,相对于候麦影片中更加明朗和凸显的人物关系,这里的色彩,镜头,背景,人物之间语焉不详的对话却很有几分靠近北欧的冷峻。
语言的运用更是,北欧棱角的语调极衬影片的凌冽。
对于色彩的运用,显示在新入的家具上,很有几分宜家的设计感。
墙边的黄色沙发。
人物对于色彩的评价,嫉妒的颜色,疯狂的颜色。
总觉得有几分暗示Jan,Mara与 之间不成关系的关系。
很好奇,一个男子在毫无感情的情况下与一个女子发生关系之后,他对于后者的感情,会有怎样的变化。
所以留意了几分第二天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还有那个耳边的吻。
触觉,里面有几处对于触觉的描摹。
没有情欲,却甚似情欲。
两人在片头和片尾交互的梦境。
两人的交流。
梦境。
梦境里的肢体接触,都很难让人猜透二人的身份。
关于皮肤、抚摸、织物。
很是关注其中出现的织物,纯色的衬衫和针织,角落里堆放的脏衣物和拾起来嗅一嗅的人。
织物与皮肤的包裹在逼仄的空间里变得格外清晰。
蜘蛛的象征意味,从一个人的手指爬到另一个人的掌线。
构筑起一丝如有若无的联系,但随之又断裂。
镜头里每一个人的五官和轮廓极其耐看。
而其中平刘海的瘦削女子,让我想起很久之前实习工作室内丹麦的女设计师,总是一袭黑衣,高个,发髻,行事如猫一般。
那一晚上party的放肆,雨夜的抚摸和早起两人似有若无的亲密。
而Mara与Jan之间错过又没有错过的情愫。
是否激怒或是唤起了她猫一般的嫉妒和占有,于是,选择将Jan推至室友的暗室。
至于Mara,总是像一个局外人一般飘离在整个蛛网之外,但是她又仿佛是涉入其中最深的那个。
桌面上的人物素描里夹杂了太多情感的注视和观察,以至于自己笃信,她对于一整个房子的活物和静物,都怀揣着隐约的艺术家的深情和欲望。
最为柔软和充沛的感情,却总是终结于近乎残酷的动作和言语,甚至有些暴力。
打死苍蝇。
她对Jan说,我不喜欢你,这苍蝇喜欢你。
但是我把苍蝇打死了,现在没有人喜欢你了。
戳破杯子让红酒浸湿简笔画。
你能感受到她对于即将到来变化的抗拒,但是这层抗拒却表达得分外晦涩,甚至有些略带恶意的自暴自弃。
钻子钻木的镜头被放大得很逼真,钻子钻进石头的艰深,激起一层薄薄的碎石,像极了被戳破的生活本质。
蜘蛛的影射意味觉得选得简直妙极。
两天一夜,分离与相聚之间的情愫和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极了蛛网,延伸,延展,脆弱,粘稠。
其中人物的关系也说得不甚分明,线索全然在于角色交错的,逃避的眼神和避重就轻的,甚至不成句子的词语里。
对于孩子和小兽的刻画,同样不带一丝个人色彩。
此外,一整个镜头和影片都是层层嵌套的凝视。
导演的镜头与轮回的人物,从背景滑向前景,Mara对于他人的注视,而每每她的注视背后,镜头一转,又是另一个人的注视。
甚至看着看着,觉得仿佛在窥探自己的内心。
逼仄,却总是被各种难言的说得出口说不出口的情绪涨得满溢。
而那一张张各异的面容和表情背后,贯穿的是同样谜一般的对话和凝视,像极了博物馆里的立体模型。
所有的感官,都用来刻画情绪与欲望。
人物之间的动作与语言变得抽象成一整个疫情时代下隔绝的疏离,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爱与恶,调笑与谎言的游离。
。
4 ) 物件、空间和疏离的人际
〈The Girl and the Spider〉译为《女孩和蜘蛛》,Mara房间里的蜘蛛是她生活的探望者,是她浸入平静之中的抚慰,而蜘蛛会消失,暂时留下了网,网呢,也终将消失。
这像这世间的所有关系,保持着恒温的状态,我们放松于对他人去留的期待,不过盛的表达之间都是懂得,亲近又疏离。
Mara陪伴着Lisa完成这次的搬家计划,在此的朋友、邻居每个人神秘又安静,目之所及大多数时间大家都是在摆动屋内的物件,而物与物的沟通、变化,展示的都是人与人的交集与分离。
房屋里人和人相伴的合照,肩并着肩,笑容满面,是联结。
胶带粘过的线,木桌上的划痕,角落的一切是人与人对关系的解释补充,是人与人不再解释后的漠然。
而Mara带来的设计图纸,会错乱,会正常,会被人添上几笔,会褶皱也会被打湿。
仿佛人来人往,便一定会留下痕迹,有惊喜也有唐突。
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是可以确认有人在我们身边。
正如Mara心中的蜘蛛,她将此分享给过Lisa,也分享给过Jan,Mara会有那么一些瞬间得到了某种明白和接受,吸引和相融,但它们很快又流失了。
我们不要因为害怕它消失就如同邻居Nora一般煎熬,守着孤独,别无他物。
我们不用想象着有人站在我们身边,也不因有如此的想象而痛苦,人生那艘船不会始终平稳地前行,我们总要被绊倒,而有人曾站在过我们身边啊。
5 ) 人类为何不团结?佐尔彻(兄弟)电影中散落一室的心灵鸡毛
如果还记得《八月处子》中艾娃漫游在马德里假期的市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朱莉置身的奥斯陆北欧地景,以及美国制片人夫妇在法罗岛景点巡礼的《伯格曼岛》。
那么一定会认识到与这类书写都市-荒野时空处于另一个端点的是那些专注有限空间和日常对话的室内电影。
如滨口龙介《偶然与想象》三个短篇中的局促场所所往往触发最开放的谈话。
洪尚秀的日常室内切片和散文式随机表达(包括《在你面前》,《这时对,那时错》)打破了电影僵化的造梦机制,构建了其作者导演的坐标系。
同为柏林影展常客的佐尔彻兄弟执导之“人类团结(human togetherness)”三部曲更是亲密格局忠实的拥护者。
如果都市漫游必然遵循了某种侯麦方法论,那么室内论调总令人回味起伯格曼场景式谈话录中溢出的多重人际张力。
后者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美学表达被不断延展实践,不仅因为有限的空间促使我们转向对精神世界的考察,而且获益于日常物,密集对白和面部特写等视觉杂糅对人类行为中的脆弱,决裂,甚至崩溃瞬间的捕捉和记录,成为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解构和批评。
继关注家庭关系的作品《那只奇怪的猫》(2013)之后,佐尔彻兄弟继续将私人情感和生活场域作为叙事核心。
三部曲之二《女孩和蜘蛛》围绕一次搬家-离别事件触发了普遍内在于人类中的幽微有毒的恶之花。
恶意满满的报复,捉弄幼小的快感,一闪而过的内疚,过度的控制欲,受害者竞争心态以及心灵深处永恒的孤独感。
恰如一次在室内刮起又消失的飓风,使这场分离的图景充满了斗争与挣扎后的黯然与狼藉。
电钻凿开地面的镜头立刻让感官温习了关于震动的记忆,绽开的裂缝暗示着破坏性力量的介入,也象征即将走向分裂的人物关系。
这是柏林市中一间正待装修的公寓,固定机位的镜头中流动着忙碌的身影:穿梭运输的工人,搬家的男孩和女孩,年长的母亲带着孩子,新邻居和刚出生的婴儿,以及满地乱跑的猫和狗填满了公寓各个角落。
交错出现的人物/动物一度打破了观众对主次关系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和预期心理。
你无法立刻判断这是属于两个少女Lisa和Mara的故事,还是属于一群人的故事。
进入这个叙事的切入点可能对每个观众都不一样。
就笔者而言,或许那个瞬间就是Lisa为了惹恼母亲而故意亲吻感染了胞疹的好友Mara。
这一举动暗示两个女生拥有超出一般室友情感的暧昧关系。
而在持续发展的剧情中——Mara回忆起和Lisa在旅行时的遭遇,两人一起玩弄蜘蛛的场景,以及相当有限的Lisa与男友的互动镜头——都让观众感受到导演精心设计的一股暗流把我们的关注点推向两个女孩看似友好,但又若即若离,时而恶语相向的矛盾复杂关系上。
在尚未意识到分离这件事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时候,电影却先行一步给出了一系列因离别造成的糟糕后果,以及这种破坏力量如何波及了周围的生态。
Mara把热咖啡倒在狗身上,在Lisa母亲使用马桶时刻意地不回避,用锥子在桌面刻下划痕,在新公寓的窗台上留下碾碎的烟头,用笔戳破纸杯让液体浸湿平面图,将带血的创口贴留在新居里,顺手摔碎了邻居情侣的照片。
这些发生在眼皮底下轻型又隐蔽的暴力充满侮辱性和攻击性,但又常常被忙碌混乱的外界环境消解于无形。
Lisa即将离开曾经的室友Mara,与男友在新公寓开始新的人生。
独自受伤的Mara不断在Lisa周身和视野内制造各种象征性且刺眼的破坏,损毁和挑衅。
看似不针对任何人但指向性明确。
她无法控制昔日友爱和亲密的流逝,便用恨意来营造一种糟糕且不幸的处境。
一种争夺注意力的俗套把戏。
这便是Mara编织的一张蛛网,上面粘满了离别的不甘,蛰伏的敌对心理,以及对昔日爱意的留恋。
即便如此用力捕捉,Mara依旧无法改变与好友渐行渐远的真相。
出演这个角色的德国女演员亨丽埃特·肯夫里乌斯以冷淡且疏离的镜头意识诠释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局内视角”,试图将观众拉入创伤心理与强迫症候群的漩涡。
同时又摆出一副“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嘲讽着人类的盲目,徒劳无功和沾沾自喜。
电影中发生在女性间的敌意与裂痕确实有其符合一般现实的基础。
因为为了迎合社会的刻板期待,女性间的对立显然更加间接和隐蔽。
电影《裂缝》发生在寄宿女校学生间的霸凌和孤立便属于典型的隐性攻击。
青春片《你好,忧愁》里的少女暗中利用父亲的花心来排挤未来的继母,导致后者死于意外事故。
前者频繁出现的是施暴者对受害者在话语和身体上的双重侮辱。
后者的报复建立在世俗-道德对女性规训而导致的必然伤害上。
这两种传统叙事都清晰呈现了对权力-惩罚体系的套用,也很容易分辨出弱者-强者的对弈话语。
《女孩和蜘蛛》并未完全迎合这种套路。
相对《那只奇怪的猫》里发生在家庭成员间挑动神经但又无伤和气的无厘头举动,《女孩和蜘蛛》让暴力现象更频繁更激烈地出现。
同时,滋事和矛盾的对象从人物波及到动物和环境物品上。
当Mara不甘被忽视而向外界施加一系列不道德行为时,电影又开始同情这一角色呈现出的无力感和虚无主义。
蜘蛛作为一个居家性质的昆虫不仅起到回应三部曲名称的作用(另外两部出现了猫和麻雀),在Mara心中更是一个代表着陪伴和期待的童年象征,对情感关系的渴望与某种生存的本能勾连在一起。
对比女孩故意欺凌狗和拍死苍蝇的行为,Mara每一次都是用蜘蛛向他人展示善意和友好,电影也用两组相似的镜头反复加强了这一行为。
相较之下,Lisa的少女感中有种志得意满的霸气,却也会在暗中搞小动作。
她当众揭穿母亲与装修工人调情,转身就把对方的外套扔在地上,毫不留情的嘲讽Mara,却又享受彼此共同的回忆和精神世界。
佐尔彻的文本里充斥着此类自身悖逆。
主人公的多重面目仿佛在玩弄观众的情绪,让我们的意识摇摆在恶作剧与塑料友情之间。
没有谁是唯一的强者或者弱者,也没有单一的施暴或受害者。
观众被迫共情这种人际困境,又渴望摆脱这种不安的矛盾。
《女孩和蜘蛛》把“破坏”稳定和惯性作为探讨人性中善恶一体两面的前提,并把人类在离别中表现出的束手无策和落空的无奈看作是必然的妥协。
作为交锋的残酷战场,新旧两个公寓的空间实际上拥有某种相似性。
一个是入住造成的凌乱驳杂,另一个是搬离后留下的废墟式荒芜。
佐尔彻兄弟导演充分利用室内场景引发的感官模糊,平移了类似的场面调度策略,让即将分离的人又持续发生交集。
不断重复的嘈杂环境,锋利的人物对话与静物蒙太奇在物理层面构成了《女孩和蜘蛛》明快且困惑的三重视听。
而多点透视,第三人凝视和镜面反射也构建出公寓私人-公共空间的双重属性。
电影的意外之喜在于它通过人物的回忆和想象在现实基础上分离出了新的空间与时间维度。
当Mara讲述在异国与Lisa走失的一段过往,电影随之从灰调的公寓楼进入一个光线明媚和充满欢乐的喷泉景观。
它即是一种精神上的提振,也是对两个少女亲密关系的一种概括性补充。
再如Mara撞到额头后,竟然看到楼顶的老妇人在雷雨暴风中发出女巫般的狂啸。
幻觉与真相,现实与虚构恰如其分地咬合在一起,超现实和灾难隐喻再次加强了视听上的震撼,导演四两拨千斤的高明便体现在此。
室内空间虽然局促,也迫使镜头去寻找一些更加细节微观的事物来调整节奏和保持整体的呼吸感。
电影收集了一系列被Mara使用或破坏的物品形成蒙太奇段落,以一种图片档案的方式再次流淌过观众的视野。
它们沾染着人类的破坏性人格,带着绝望而孤独的气息。
被邪恶化的工具。
被遗弃的纪念物。
一切终将随着离别的到来归于黑暗与沉寂。
《女孩和蜘蛛》有着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对所探讨的问题和概念保持了高度专一和纯粹。
两段式结构的克制反而让视觉语言的发挥更加轻盈。
偶发的故障,行为的对耦和诗意的文本都成为承载沉重现实的着力点。
即将到来的人生就如Mara想象中的那艘游轮,恰到好处的承载了女孩身心持续坠落的失重感。
此时,善与恶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在不由自主的代入中,我们都变成了那个轮船中的女侍者,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接那无止尽的颠簸和惊涛骇浪。
6 )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互相伤害
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尤其是需要长时间相处的时候,自然更加重视某一种零界点,如果越过了这个零界点,那么关系自然以糟糕的结局收场,反之,人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这种纠缠就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作为规范。
所以,纠结的人会多一点。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女孩和蜘蛛》讲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问题。
一对住在一起的好姐妹就快要分开了,两个女孩原本关系很不错,然而当分开正在进行时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瞬间变得微妙了起来。
短发女孩面对着长发女孩的离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错觉,就好像这一切与自己无关,然而实际上这种关联还是不小的。
而长发女孩显然知道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又能怎样呢?
她努力地避免着刺激短发女孩,然而她却避免不了事实的侵袭。
两个女孩之间的有了矛盾,但谁有也说不出来矛盾是什么?
周围的人群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看似与搬家有关,实际上却是每一个人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一种预判,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进来了,有的人分手了,有的人热恋了。
《女孩和蜘蛛》为我们描绘出来了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络就如同一张蜘蛛网一样,身处于这个网络中间的人都愿意成为那只可以决定一切的蜘蛛,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看着蜘蛛织网的人,一个并不能决定蜘蛛行为的看客。
人际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实际上可以简单地进行情感划分,与自己情感相近的人和与自己情感渐渐拉远的人。
短发女孩看似对于身边的一切都不敏感,实际上却有着一种极端的内在的需要发泄的情绪没有被正常发泄。
短发女孩的内心非常的微妙,然而微妙的内心并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情绪被宣泄出来。
于是,我们能看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场景似乎都跟短发女孩相关。
短发女孩自残,短发女孩虐待动物,短发女孩对于屋子里的家具偷偷破坏。
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实际上被屋子里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孩洞见,然而小孩并没有像大人一样将这视为一种情感的宣泄,而是仅仅当他是一种奇怪的行为,这个奇怪的行为恰恰是短发女孩宣泄自己内心的一种具体表现。
对于长发女孩来说,这个离别虽然痛苦,但是却对于自己来说是有益的。
这也是为什么她看上去总是觉得对于短发女孩有所亏欠。
因为离开的是她,留下的是她。
这种离开和留下之间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关联,关联之外,我们看到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事实无法理清的逻辑。
然而生活中的故事并不会一件一件地接踵而至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与我们所经历的都有着明显的偏差,本片也是这样,当短发女孩觉得长发女孩的离开是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男友已经快成为过去了。
当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需要一些情绪来帮助自己发泄一下的,但是当很多负面的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又无法将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宣泄,以保持自己内心的清爽。
生活总是会给我们一种答案,但答案的本身并不具备一种指导意义,甚至于很多的时候,答案只会撕裂生活,创伤如何弥补?
这就只能依赖自身的愈合能力了。
当生活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会有短暂的错愕,这种错愕看似跟生活无关,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延迟剂。
我们无法修补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漏洞,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些漏洞的时候,应该看到更多的可能。
生活不止一种答案,面对离别的时候,同样可以做新的期待,面对未知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让这成为一种心情的点缀,未来总是会来,那么未来又何来恐惧呢?
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依存就是相互伤害,短暂的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一种奢求,因为当所有人将表面的情绪变得平稳之后,并不代表他们内心之中也是这样的稳定。
波涛汹涌的内心却用风平浪静的表面来表达,长此以往下去,总是会有撑破的一天。
如何相处?
如何面对?
如何接受眼下,如何畅想未来,或许生活不仅仅有一种答案,我们接受了,也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你好,再见
7 ) 你,怎么在这儿?
布萊恩早上開門照例去丟垃圾,吱——嘎——!
門的老荷葉響聲刺耳,他眉上就是一縮,躲門后的他接著想到剛搬來的鄰居,謹慎地開,鋒礪的刮音更盛,他只好閉眼,睜開的時候,門外已經見到光線,心頭卻感到詫異,因為那幾個前天昨天的垃圾袋沒了。
他害怕是他哥哥來過,又不全信,把棕門敞得寬了些,慢慢地發現廊窗,電梯與墻的拐角,跟新鄰居同時出現的舊酒箱。
兩個垃圾袋,一個映光,一個埋在破綠紙箱陰影里。
他人整個不得不走出,來到門外,在廊窗和上樓的梯臺間,那處這一層最亮的地界,歸整下第三袋垃圾,然后原路返回,由他這個人寬度大小的門縫進去。
提醒自己再扔的話,盡量離開門,這里已經停放了401室的車子。
布萊恩從這月的中期,在社交網絡上接聯換名字。
不論一開始的他看他頭頂的風,中段的取自己名字中一字后綴個的,到最后認定一個讓人眼見后瞻顧想象的,都使他回憶童年一段不愉快往事。
這三個名字常使他想到哥哥。
布萊恩五歲時候,在甜蜜的童話時間里,曾和站身后的哥哥,共同觀察過一只暖箱里的土豚。
起先,他極為排斥這次他哥哥口中稱為的旅行,就算他親自和土豚對視,他還是怕晚上做夢,感覺不出哥哥口中說的可憐。
透明箱子不大,里頭看來看去也是一只,哥哥欣賞得高興,忘記平日的怕前顧后,布萊恩幾次回頭,小身體快貼近暖箱,以免再讓他哥哥蹌上后腳跟。
與土豚正面相撞的剎那,他盯著瑟瑟厘動的粉鼻頭子,越來越害怕,但從玻璃上認出個陌生的哥哥,臉像蘋果。
這是最后一次關于哥哥的清晰畫面。
他沒想到,前兩個平臺更改的輕松來到最后一個卡殼,要求是逢到月底。
他想二月只有28天,論理過了這天就可以,可是等到3月1日都不允許,他看著面熟的粉紅警字,似乎那只土豚盯著他,他手一敲,字閃現即滅,像土豚的鼻子。
他心慌了,來到街口想起關機后網線的接口沒套塑盒。
就打算多拐個街區,呼吸點新鮮氣,壓壓驚,再到小酒吧去擦桌子,洗酒杯。
原先到酒吧不消三個路口,但都是小道,踫上的人也少,等他都拖完木地板,抬眼從吧里最方的玻璃看出去時,他還會如愿見到棵香樟,叢叢萋萋,會想日本有個山也有座橋,叫吾妻。
其他時候,他從這里將目睹可怕的一幕,他哥哥站著,宛像棵樹。
他不和那對眼神對視,接著低頭混淆念頭,那根本可以表示至親的人,不光是愛人。
今天這條路太直, 也寬,陸續逢迎了三個怪人。
第一個是個青年,身形利索,穿著遮住膝頭的純黑呢衣,布萊恩一見這黑就想這種黑料子下水不會沉淀,接著他看到盆血紅的染水,馬上搖頭,清了清視線,這人腰上斜挎扁包,土黃色,但是雙手抄口袋,腿用力猛,扁皮子有時鼓得高,許多橫截面都是光。
他很高,但神情落索。
第二人是個背影,前罩劉海,一個半身白夾克下攏黑褲,腰很細,一路向前,不卑不亢,布萊恩因為他步子莫名得快,有一會回頭發現落開許多人,他們和他相反,縱然是疲憊的步態,緩緩默默地走。
等到見了第三個人,天上下雪了,他黑衣黑褲上開始灑霰子,布萊恩一直想辮別他的長相,但他不給,始終低著,頭、頭、頭,布萊恩產生同情,和他交錯一時間,瞥見后者貼緊褲縫的大手。
最后一個人跑過去了他才認出那么荒誕的裝束有人膽敢穿著經過大街,肥大的墨綠格子呢褲上邊是黑西裝,用倆個手慌亂地朝腋下的個黑包掏。
布萊恩行走著想著忽地意識到,這雪越下越大。
他想這次再上萌蒂那講講這一會兒的感覺,因為他不能確定到底下在哪年的雪大些。
上回萌蒂問布萊恩真正見到哥哥時像什么樹,他長時間看窗,讓萌蒂好一會兒找,以為外邊應該有他潛意識中想說的樹,但看出去,都是些常綠灌木,個長不高,她回過頭。
忽然想到坐的地方,是不是該換下位置,離屋中盆栽橡皮樹遠點,這樣布萊恩就沒有機會看窗,這樣就能讓他得到更好的心理治療。
可我要說這么多場雪,她能搞清楚我的意思,哪個表達得重,哪個是單獨從我這剔除的,只讓她也有機會感受一下屋外,因為每次進門我都看出來,她又一個人待那屋很久。
酒吧牌子邊燈捎上些雪粒,遮了半個字,布萊恩見到感覺出奇冷,他開始躲蔽,扭開頭,就發現地上薄薄一層雪映了酒牌子霓虹,那缺了的半截正好在雪地上浮現完整,布萊恩拼出了哥哥。
他記得他一開始是想繞遠,第一眼倒正,他感到窒息,身子失去平衡,一倒腳頂上根燈桿,雪成片顫下,落鼻上、臉上,后來他眉心也感到涼,平靜下來,抬頭看天,漫無邊際的雪沒有聲音下降。
你在干什嘛!?
布萊恩恍然,這是在路上。
隨口答應,往酒館方向站直,整整衣領,帶著一身淺雪進了門。
小老板繼續回到里間,背影讓布萊恩生疑,他后來出來,布萊恩不敢張他,他根本沒有看他。
第二天清晨,布萊恩下班,扔夜間廢瓶子,瞟見那三袋垃圾上壓了個鐵銹窗框子,放下了心。
晚上接了萌蒂電話,約好明天白天到她那,時間任由布萊恩選擇,這一整天沒有其他病人。
放下電話,布萊恩想這種每周一次的見面到底是加重了看到哥哥的機會,還是已能徹底抹去這個人。
如果說要抹,那最好都有必要清零,連上那個5歲,那個落日,那條通小鎮博物館的路,即使有上百棵再珍貴再讓人懷念的樹,布萊恩都不想要。
后來他想到5歲到15歲,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穩遂的時間,他到現在都不敢確定那個時候有沒有哥哥,是不是因為活在一種憧憬中而顯得勃勃生機。
他摁動那面白門上的鈴,視線就停在每回感覺怪異的圈花陣,有一年,好像是有年冬天……他突然為這個年齡能想起哥哥那雙沾泥的鞋子感到種羞恥。
這個時候萌蒂開著門,看到布萊恩半低的臉上愁容上來,嘆了口氣。
隔著安靜的街道,布萊恩后身有棵桐樹,底下匆匆跑過個人影,沖她半空劃圓,萌蒂用眼神提醒跑者,看著他點頭火一般遠了,布萊恩目光接上,問她還是上星期她口中晨跑時看出她孤獨的那個人么,視線不等聽完她的話就滑了下去,神情落索。
一进来,布莱恩首先发现那株橡皮树不见了,人走过去就坐下。
萌蒂整压坏的裙边,发觉少了点什么,半天想起以前敏感的布莱恩没注意到树,还是他一直就没发现有棵假模假样的真树?
布莱恩看见女孩子很窘,说怎么了,要不我下次早点。
萌蒂这笔帐开头开得诧异,叫他一续,反不知道自己想到哪了,干不干挠接下去的治疗,弄得她更窘迫,这个……放膝头的细手两边找,含含浑浑地指一个方向,布莱恩不明白她,只好撤撤座椅,一会儿气氛纠正过来,她看眼窗外,一张绿叶子旋旋着下降,听見一种轻微瑟缩的声音时这片叶子蹭到窗戶,裂了個長線,開口卡在了磚石凸出的釘子上,殘葉子伶仃,她意識到布萊恩還是憂郁,就否定他,那個不是你哥哥。
怎么不是,他就知道那天我晚到,他等,等牌雪厚到時候,剛剛蓋住,他用棍子戳掉半個,盯著我,遠遠看住我,我恰好走到下邊還沒接近下邊,他讓雪震下去,霓燈再一照,不那么明顯,一切像自然而然,然后我就能看到哥哥這個字。
這怎么不由他一人導演。
布萊恩第一次哭,萌蒂萬沒料到,有些可憐他,只好假裝不見,低下頭認真記錄。
一會兒他咽下去了,注視剩下的半張葉子。
你這那棵樹呢?
什么?
哦我送人了。
這種樹有人要么?
什么?
這是好樹,不是任何人能餋好的。
不如我見過的窗外樹,香樟。
萌蒂忽然記起他說過,讓他再這樣勾動幻覺,等于本回療程宣告失敗,就沒接話,一話到底直接問他這周吃藥時間,不要像從前,吃一半扔多半瓶,那都是欺騙自己。
吃這樣藥有用么?
有什么用?
只能讓我脫離現實。
你現在做的正是依靠藥物扭轉幻想以回到現實。
回到現實?
真實的冷冰冰的世界?
讓我乳房發育,停止想念,戒除感情,見到他前從不讓我有所準備,然后忍受不負責任的訓斥。
布萊恩你準備什么,你哥哥他并沒有出現。
你知道什么,他的長處是飾演,上周他搬演的警探根本和90年代最著名那季的演員毫無二致,這就說明,他會以任何一種形象突然站到我面前,而我可能以為他是個和藹老人,跟他掏心窩子說完都不讓我發覺。
那又有什么不好?
這證明你還有哥哥,他關心你,他害怕驚動而不得已采取這么復雜的露相。
這有什么不好,這是在挽救。
挽救?
萌蒂后悔了,布萊恩遞完這倆個字后頭深深埋在臂彎,就過去想拍拍他肩頭,布萊恩的聲音從深谷里偉上來,這次可以了,下次爭取早到…… 他在路上就發現原先準備好要說的話一句都沒講,他在看第三個男人就有的想法到現在,自己辮認出來,是他自己,于是他看雪。
他記得,雪突然拍到窗子是上次,窗臺邊那時還有那株橡皮,這次來,外邊繼續下雪,他坐的椅子和大塊玻璃間很遠,他一度用眼去量,缺了樹,還是一米半。
有時他感到冷,不過從沒給萌蒂提,她看出來,但總在我想得到什么的時候她低下剛想溫柔的眼,去看那個破小本子。
她讓我常身上帶個本子,再見哥哥,把我想的,看到的,他的,他又怎么說統統記下去,一本不夠本子有的是,要知道記下的就是珍貴的,想見的時候不會嫌棄搬開抽屜的次數。
我當時說我抹桌面時經常會踫到,可我沒有時間再描畫,這個經常能讓她卡殼的提議上一次還是被她看窗外打斷了,那時也正下雪。
我不想念雪,一點不想念,守候母親,等待父親,11月剛進下的圣雪也不留戀。
布萊恩這晚做夢,他又見那座山,明明是夜雪,山頂沒有積,山身也不見零雪。
他看著夜寶石藍的天,待在五樓屋里,孤島,雪枝,積雪坡,夜里第一行腳印,他開始討厭那個壓上鞋印子的人。
地上從坡高直到坡底,一腳跟上一腳,雪大約下完整一個小時,印子轍里沒有雪,大雪是忽然停下的。
有銀邊的楓樹,山路拐彎蓬松著雪球的晚櫻,他嘟嚷著童話童話。
一路長坡剔透,他后來看部電影,上字前一種仿核酸羅旋不止的鏈條,人眼當張見寬面,每個觸頭頂端,鑲了四指指甲蓋大小的鉆,繽紛神秘,跡動明滅,那個坡就是這樣。
夢到這里就醒了,他感激這個夢,沒讓他往屋里走。
煮早間咖啡,布萊恩在陣陣冒泡聲中譴責了自己一回,怎么還是保存那年那個時候不該有的心情,即便做夢,又讓他好像重聽一遍母親隔屋問他你找什么?
他翻了幾個陽臺箱子,找不到一本古詩,就說什么沒找,旁邊就是幾年后常讓他做夢的窗子,下雪,打雷,紫色閃電,夏夜高燈桿梢的黃光,沙沙刮過燈罩的長雨滴子。
晚上酒馆打烊,时间一早,他反不适应。
慢慢腾腾到后间找风衣,摸来摸去都是那件,土黄薄布,老板过来幾次看杯盘收拾情况,又见早該半小时前离开的布莱恩,恍然问他你又走不了了,末尾輕聲叫上几句布莱恩。
怕他光盯头顶小灯罩着的光犯上强迫症,上次就是,往外倒泔水,瞅住绿果皮箱子,等回来时托盘上粘着一滩热乎的香蕉皮。
我没事……他神色谌然,这倒让乔治很不知所措,后者见他脸相十分后悔,他那么高大,却经常受伤,乔治第一次留住他也是这种道不清的恻隐心。
那你怎么不回家,外边……乔治没看到窗,小间雾头头的,惟一光源还是布莱恩因为身躯的长度推大了点门而比平时多闪出来点酒厅光。
乔治看到了这光,觉到一阵孤涼,默默走到一溜插杯,拿起倒罩好的看看里邊的底,一個又一個照原樣扣回去。
布萊恩在他身后,卷捏著衣角子,說出的字斷截落塊,你,你剛才說,什,什么。
他剛想回頭,布萊恩擦著他后左肩蹭出了門。
剛下過雨,這里沒有花樹,布萊恩向更遠的高大楊樹眺望,卻聞見陣丁香。
夜風伶仃,剛下完雨天洗得深藍,這讓他琢磨。
雨后,不是深粉就應是米黃,它怎么又是藍的。
莫非哥哥,是他又……回來了。
一顆楊心葉子追趕上顆綠心,梗子弱,一重疊像心臟,心臟是這種形狀不是,它沒有紋路,路,長的,彎下來,支脈豐沛,輸送水份。
我將在這酒館子里走路,將要踫上他,離不開他,離開她,再給他說再見,這條路不長,但能短到哪,不久開始分岔。
總是不久不久。
翩燈翩燈,嘩匹嘩匹。
這種聲細碎,縷薄,布萊恩的脖子滲入幽岑涼意,他想到不管早回晚到家里沒有人,是不是應該聽萌蒂的老話養上條狗,他喜歡導盲犬,白的。
布萊恩縮進脖子,試出早上剛換的領子仍然漿挺,白天出過那么多汗,還是不需要一條長毛的狗。
他聽著,連綿不絕的海浪一碧一黑,很薄的離開,厚重的窩在心子里上不來,五內鼎沸,翻涌不止。
他將就著低頭,眼前幾步就是垃圾筒,腳底多壓十步將踢上扁罐,他閉上眼,不想看日間手里摸索了上百次的啤酒名,忽地聽見哥哥,他站在土豚前說再過十年,動物拳手呵暖,他認真地看著,或許五年,就離了這里,可能會喝酒,那個父親常喝的畢立牌。
布萊恩瞇縫眼,腳尖使勁揚高,瑟縮的、寒冷的、鐵踫水泥的,熟悉,痛恨,記住,都隨著孤伶的鋁罐子滾遠。
小罐太輕,攀近前頭棵碗細香椿一路巔巔波波鏘回,最后被個淺坑逮牢,左右晃了晃,絆地聲清靈,布萊恩感到渾身在發冷。
他不知道眼里什么時候出淚,背過向風,睜開眼淚水刮到地面,他發現在他后身,一對腳站著,挨住下一個垃圾筒。
那個還是他。
布萊恩這次不像以前,將頭朝向的時間延長了,竟發現這是個女人。
每天大約應是從傍黑天開始,這人就讓布萊恩在正沖窗的吧臺下,或起身遞酒,有時又給人寒暄的時候,發覺干凈玻璃上有個點子。
有時是綠,有時是黑,但都是毛邊不齊整,霧轟轟在標牌最大字母和末三行拉丁文附近摸索,升高,落低,有一次他聚了聚光,終于認出是個人。
從這天開始,他能經常見到他。
但他一直以為她是個男人。
身形寬厚,又長又扁的個草編落伍帽子,斜吊住頭頂,在垃圾筒旁邊,像家像驛站的蜷腿夠東西,這總讓玻璃后的布萊恩想到慘這個字。
這字第一次出現時布萊恩11歲,他追晚霞,才知道離家不遠,每天必走下去的坡道拐彎,居然能有個住在斗屋里的臟老太太,以后常給她送吃的,煤油燈忽滅忽亮,小布萊恩以為那個屋沒夏天。
白天出來酒館,布萊恩站后頭看他會兒,他看不見他,十分滿足地仰臉吃手上吊下來的豬肉片子,油流一手;晚上出來,布萊恩豎起領子步行回家,經過他被他叫住,在伸出來的臟手心里,放上十美元,再看一眼紛雜亂布的紋路。
布萊恩掉頭回家,哎!
你。
他又生上氣,回頭眉毛撮團,夜風驟然呼嘯,他眼眨都不眨。
那個人的粗手一點一點地,離布萊恩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布萊恩吃驚地看她眼,半張嘴。
黃色的霧,黃色的天空,左肩膀外的高架橋是黃的,酒館、雜草,布萊恩感到站在個小坑,他呼進的氧氣、呼出來的氣,都是黃的。
你怎么還要……!
她今天穿著寬松的薄裘皮敞衣,一溜七個扣子掉了仨,剩下的系得歪歪扭扭。
扣邊抹實層油,油邊油袖油領。
她眼神和藹,向布萊恩射來致命之光,正是這種過去不能忽視的光,讓布萊恩給過錢后總回憶些不好的往事。
回到家想起來讓他十分厭惡,因為這里邊都有哥哥,過后就是吃驚。
現在他不能再忍受,即便一刻也許就能會使他回不了家。
布萊恩狠上心,一掄長胳膊,在她失望的目光中繼續給了長長背影。
她望著這影子,讓它走,不讓走遠,將到線桿了猝然給了句布萊恩——粗粗的,前端薄,后邊的冷峻,熟悉可怕,當不愿聽到和極為憧憬之間界線模糊,這種跨越反而更加重了恐怖,讓布萊恩最后殘存的一點子愿景都抹滅,他縮到領子里抽泣起來,不敢回頭。
他跟着他回家。
布莱恩驽着劲,憋住,快速溜街灯暗地儿走,他更知道不管他怎么挑道他都不会甩开他。
他这是铁定好的,从那个辽远的家乡,一个村里,早一月或俩儿月就合计,我該哪个晚上,在这一晚穿上土黄色裘皮,这样当灯光是黄的,可叫他一惊间回到这个村,在这个村里沉没,我可以教导他,一直到他死,或死去。
你为什么非得这样恨!?
任凭个小干巴鸟儿它的兄弟都不会扔掉地上的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布莱恩此刻眼前生雾,他想在这条街头最后一棵细瘦桂树前见到萌蒂。
可这又怎么可能?
那我明天还有这个必要亲身去见她的么,我最恐惧的,我最害怕的,我一直希翼的一直盼着的哥哥,这个最打击我最了解我的人先于她,她说过的一切正朝好的方向走,慢慢会变好的前夕突然降临,那我的明天……还有明天么,就这晚,这段有昏惨惨夜灯的土路,又是土路,土豚!
我会死在这里!
可是我还得要走完这一条然后也还有五条路等待我,才能进到那个保护的窝子。
我該怎么办?
怎么办!?
有时,布莱恩走着,感受刮到领子一路窜向中腹的强风,会想我的身后是不是早没了那个人。
但他不敢随便回头,盲目的,顺从的,像有一根线,你只要认定这个前边的方向,那他就是你身后那人的敌对,他会怕,把怕转嫁到他身上,让他也尝尝什么是恨,什么是裹蜜后的苦。
他会退缩,悄没声地退,以种他眼中你常有的怂样儿,这样你就可以是他,他变小了,那个张着呆眼的土豚就永远呆到童年。
我还有双灰力鞋子,他总说我会用到,会用,我穿了一回从不让我洗掉说接着还要穿,然后它就在床底一个纸箱子上蒙尘,一呆就是半年,这半年我都经历了什么,他总能在我想拿出鞋子时出现,他这是控制。
但是这个事萌蒂不会当做什么重要事,我不要说。
布莱恩猛然发现他的手指尖很凉,低头已来到那个白铁门,光滑的表面一尘不染,他手中钥匙原地打转,卡楞楞、布呤呤,冬天寒风中显得清脆。
一切都脆了,我辛辛苦苦构建起的这一年,只在这一晚,年末一个冬天轻轻地就打破。
布莱恩转身,关门,抬胳膊,放大衣,摁了摁自己衣服上的扣子,放了心,原来他没想错,那串破銅扣子在他身,怎么他也还没再婚?
然后布莱恩想给自己沏杯热奶,就用前天刚买的印艾菲铁塔的那个白高杯,想到这他突然想到萌蒂也已经成家了。
一路沮丧地摸着地前行,没开灯,几乎跌跌撞撞地啪亮了壁灯,忽然他感到一道冷剑光,他干净的眼受伤了,他保护了一年的这个永乐乡,渗入了……终于进来了。
身子差点整个摔到地,但他感到身后已是坚硬的花缸,一个接一个,都顶着他: 你,怎么在这里!?
老妇神情柔和,换了个人儿,此刻屋小,她倒也试着自己寒酸,不再像户外,十分落魄。
在每句话间偷偷看他一眼,是个女声,布莱恩听着,渐渐地听,她因为想他,每天为不担误他的工作,都在默默关注。
你不也经常在那块玻璃夹儿上看得见我么?
那你是谁,你……布莱恩开始上气接不到下气,你跑来,胆敢,你,怎,么能……啊,到我家里来……说这个……你这是,在逼我!
…… 布莱恩以为自己正在说这句,但不久发现这只是他的想像。
他发觉后更加害怕,一阵哆嗦先从嘴角那里抽。
是了,是了,他知道,就他一人知道,我的嘴特别敏感,甚至要的命的……布莱恩马上感到呼吸急促,他怔住了,呆看女人,女人鼻子有了饼样,眼无限往两边扯,整个屋子在他眼前天旋地转,他的眼在找镜子,他站到长镜了,他后边是窄条豆沙色沙发,沙发后是棵小榆树,榆树后和寂静的街道间只剩一窗。
他嘴颤停止,他呼吸停止,他非常悲凉,绝对悲悼,绝对伤心,一股风从镜中开始刮下,风碎成箔片子,傾刻间覆盖镜中所有的家俱。
布莱恩喘上口顺气,打开门,朝左看,是排静静的绿色垃圾筒,朝右那将是明天路过的椭树。
他闻到洗洁精的呛鼻子的香气,蒙阍过来,门扭上的手指边缘被风呲鴷,竖直的薄皮宛若刺,他下意识地纂了纂拳头,嘭——带上了门。
从那天过去一周还是就是一天发生的那件事?
萌蒂听着,心里问。
布莱恩始终让自己的头狠狠地看窗户,窗户边的橡皮树叶子老框个半圓,这样,或是对街树下走来一人,还是突然就在窗前,落个争食鸟,都像马上要到另一个世界报到。
散步人走着很愉快,在接近叶前没有改变态度,她没有惧怕,对新生事物毫无保留,傾刻交出。
然后再不回来。
你说这是浑绿,还是沾到一块儿的绿?
就是那种,加进些,是突然,突然地进入,显现出的绿,它的边和白不到一堆,伫着。
还是已经从A到B完全地合,那截当初瞬间相交的点也找不到的浑然一体的绿?
萌蒂也往窗外看,但不打断,继续听。
我好像还是傾向不到一堆叠,是叠,它是应该重叠,但是。
你看这个女人,她是突然出现,叶子也是,叶子已经放置一段时间,还是这样,她身上穿的,有红有紫。
他没再发出声音。
萌蒂脸上放松,因为在她眼中女人身上色彩和绿融合的很好。
他再岔开她都没打断。
这只能是两天后,我再次看那位女士,她大胆地根本没想躲避,然后我和她用眼神,只有眼神,确认要在那晚进行一次绝无仅有的旅行。
偷辆车子,骑出十个街区,狂奔,车子又不贵,逮着也犯不了大事儿。
那不可能只像你说的一点感觉没得到。
布莱恩什么也不说,他想他可能是有点运气,在五年前?
在十年还是就是十五年以前,有个黑夜,绝对难忘。
构成黑夜的要素不过是风,数十年前几月前几百年前,风皆一样,凌厉、偏颇。
我用了偏颇,到底是谁偏颇,谁在偏颇,谁……布莱恩不知道这时他眼球迅速滑落,面目忽然寒酸。
萌蒂差点兴奋地掠近他,给他张纸,但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在她眼中,他说,谁在那个晚上开始偏颇。
等等,那个晚上有没有他,他在穿着什么。
夜色中都是土黄,像土葬,漫天倒下,有双眼,很亮,他竟也在车上。
布莱恩吃惊表情像个小孩儿,半张嘴说,身子前张,整个身子优美,随时会跌,随时我都在看。
这只眼光没在看我,他告诉我一直看前方,其实那晚我就听见了。
你,没把她当作他吧?
没有。
这怎么会呢。
布莱恩突然感到什么,捂嘴瞪着萌蒂,巨大的凉意遍披身躯,他却感到不久即可见到晚霞。
难道一直是他?
萌蒂也用眼神应了应他的。
布莱恩连连摆着手低着头请求萌蒂可不可以给他点时间,我需要时间。
就只需要点时间而已。
一周过去。
两周过去。
萌蒂还是天天晨跑,还是在中段能看得见自己那个摆放橡皮树的窗户。
但有一天,她突然刚过窗户想停下来了,回头等了等那个经常在窗户里头可以踫见的男人,他也在跑步,总在后头。
一切开始很难。
一切总在开始很难。
布莱恩有时在早上开门时非常不好意思,这时像个女人,他身边是他哥哥,真哥哥,高出他头一个的大眼睛哥哥,不再是那个穿破裘皮的老妪,不是那个身影瘦长极度敏感的三个男人,更不是那个滾远的易拉罐子,更不是那个酒馆的灯。
但某一天,还在秋日,他被阵不太强烈温温柔柔的敲门声打断回忆,门外是靓丽的萌蒂,她在笑,正巧一束太阳闪过对门高大的绿树,照在萌蒂头发后头,这样在她一整个头颅边上有光。
他发觉这天她的笑容最温暖。
他可以看见她身后的树,是棵单纯的香樟,可以看见一条街道,不过是灰朴朴的晒着太阳,可以看见树下一个小而圓的垃圾箱,来了个人儿往里看着,然后他和这个后来抬起头来朝他对视的人笑了笑。
他忽然可以看见了许多了。
8 ) 最后
自从我在这艘船上 我就感到头晕 它总是摇摆不定 我摇摇晃晃 惊奇地发现自己不会摔倒 惊奇于没有人摔倒 我问我自己 大厅里的蜡烛是如何做到不倾斜的 花瓶是如何不从桌边滑落的 这些灯都不会撞到墙上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磁力 仿佛一种神秘的力量 把一切都凝聚到了一起 这艘船有自己的力量 他像一座雄伟的城堡 在波浪中前行 在梦境里平缓地漂浮着 我的梦境 我从中不断醒来 因为明亮的阳光刺穿了我的眼睛 直射海洋 所以 我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船继续漂浮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只有在夜晚 才能让我闭上眼睛 轻轻地摇晃着我入睡 然后我就想象着鲸鱼 海星 海葵 所有这些奇妙的生物 我漂浮在上面 我想象 有一天 沉入其中 沉入到这个寂静的黑暗王国 这是在召唤着我 到现在 我在走廊里绊倒了 穿过大厅 船舱 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一切都在摇晃 也许是来来往往的游客 在我朦胧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 只有海鸥总在那里 自始至终 我在外面的朋友们 他们叽叽喳喳嚷个不停 我想着我的钢琴 我想象着有人在弹奏它 伴随着海鸥的歌声 我望向大海 我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因为我想象着有人站在我身边 当月光洒落在我们周围时 所以 我们站在哪儿 听海鸥的鸣叫 就像他们在唱歌一样 一首不寻常的歌 一首只为我们独自吟唱的歌
9 ) 【柏林专访】女孩的欲望与疏离,编织充满神秘吸引力的蛛网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抛开书本” 奇遇单元的《女孩和蜘蛛》,是我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最爱的电影之一。
从预告片开始就被女孩的眼神吸引,脆弱、多情,又如孩童般天真。
“我不喜欢你。
但也许这只苍蝇喜欢你。
我现在把它杀了。
现在没人喜欢你了。
” 女孩Mara这样对喜欢的男孩说。
她渴望亲近,但爱而不得的恐惧与痛苦又让她疏离。
她的爱是躲闪的。
《女孩和蜘蛛》就像一场亲密之欲与分离之痛的舞蹈。
Mara的室友Lisa要搬走了,她的心情如过山车一般起伏。
影片从Lisa搬去的新公寓开始,Lisa的母亲与Mara一起在帮忙搬家具。
在忙碌中,渴望、秘密的欲望和紧张的关系浮出水面。
Lisa的母亲与搬家工人Jurek打情骂俏,而另一个搬家工人Jan与Mara之间也产生了一丝情愫。
晚上,Lisa在旧公寓与朋友们组织了一场离别派对。
Jan也来了,但他并没有和Mara走得更近,而是和邻居Kerstin睡在一起。
她的室友Nora,一个像鬼魂一样诡异的女子,也默默渴望着Jan。
第二天,Lisa终于要完成搬家,她和母亲的矛盾却越来越多。
此时,Jan成了女孩们欲望旋转木马上的一匹马,在她们之间被轮流牵引着。
还有楼下曾经把邻居家的猫私自藏在家里的老太太,街对面药店里的年轻女孩,曾住在Mara房间里的神秘侍女,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都让Mara感到莫名的吸引力。
她对情感连结的渴望,让整个房间就像一张精巧又脆弱的蜘蛛网。
Jan、Mara与邻居Kerstin 瑞士双胞胎兄弟雷蒙·齐歇尔(Ramon Zürcher)和希尔万·齐歇尔(Silvan Zürcher)谱写了一首诗意的人际全景图,在日常生活、童话故事与脆弱世界的心理描写之间徘徊。
人物在脆弱世界中游走,仿佛被欲望所驱使,在这个世界中,伤害与亲密一样可以迅速被施加。
他们的前作《奇怪的猫咪》就已经很流畅地描写这种公寓琐碎日常下奇怪又可爱的群像了,这部又进一步风格化,把噪音、静物,来来往往人物的语言、动作奏成一首轻巧而又诗意的奏鸣曲。
齐歇尔兄弟有一个“人际亲密”三部曲的计划。
在《奇怪的猫咪》《女孩和蜘蛛》之后,他们正在筹划第三部作品《烟囱里的麻雀》。
在本届柏林电影节,《女孩和蜘蛛》获奇遇单元最佳导演与费比西奖。
我在柏林电影节采访了齐歇尔兄弟,听他们讲了许多对于创作细节的诠释。
导演们本人也像片中的人物一样可爱呢。
导演雷蒙·齐歇尔(左)与希尔万·齐歇尔(右)【柏林电影节专访】 笑意: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风格,很精巧微妙的感觉,不管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是影片中的世界,结构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正如片名《女孩和蜘蛛》。
首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
并且是如何架构这个故事的?
Silvan: 我们开始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是在2014年,当时我和Ramon还一起住在一个合租公寓里。
我们是双胞胎兄弟,但后来我们有了分开的想法,试图切断我们的共生关系。
实际上是Ramon搬走了。
这样的情感是很令人疲惫的。
这是创作的背景,或者说是这个剧本的出发点,也是设计角色和故事的基础。
关于影片的结构,其实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
我们会先堆砌一些元素,比如人物、场景、故事,还有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都加进去,然后开始雕刻它,把那些与这个世界不契合的元素剔除掉。
所以我们构建故事的方式并不是很有逻辑,更多的是联想,是比较直观的。
蜘蛛网的结构是很早就有的想法,我们希望在各个角色之间与公寓、动物和故事建立联系,然后开始构建这个世界。
Ramon: 我想补充,当Silvan开始写剧本的初稿,然后我们开始合作时,就已经完成了两天故事的结构。
第一天发生的故事,主要在Lisa即将搬去的公寓,而第二天的故事主要都是在旧公寓。
一般情况下的结构是从旧的地方移动到新的地方,但我们想从新的地方开始,再回到旧的地方。
笑意:影片中有很多小细节和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不同的噪音,婴儿的哭声、狗的叫声或者水壶的响声。
为什么加入这些元素?
Silvan:对。
其实你说的这些元素,是本来就写在剧本里的。
这些声音,比如狗的叫声,它主要是触发一个眼神的动机。
我希望片中的角色因为狗叫声或者婴儿的哭声而看向某个地方。
另一个原因是,噪音可以是故事情节中的一个元素。
楼下的邻居叫Karen,她上楼时带着一个婴儿监护器。
婴儿的哭声通常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甚至是一种相当具有破坏性的噪音。
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可以作为一种声音元素来丰富场景。
Ramon:因为一部电影里呈现的往往只有画面上的东西。
噪声就是银幕上的东西。
但当你听到一些不在画面上的东西时,就不仅仅注意画面上的东西,还有视野之外的东西。
我认为这很有趣,画面并不是全部,还有更多的东西在画外。
这增添了复杂性,也告诉观众,不要总是把注意力停留在画面上,因为画面外总会有事情发生。
笑意:影片中还有一些刻意追求的“不完美”的东西、错误或是故障,比如女孩嘴上的疮或者电脑显示的错误。
这些“不完美”背后有什么想法?
Silvan:其实这些错误或故障,是因为我们对破碎的世界、分崩离析的事物很感兴趣。
事物的崩坏、毁灭,比如Mara的受伤,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电影的主题有很大关系——统一体(Unity)的崩塌,个体渴望与其他人成立新的团体。
我们想以更直观的方式表达。
Ramon: Mara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当她的内心世界陷入危机的时候,在外部世界,则表现为她的指甲与额头都受了伤。
那些错误和不稳定,更贴近Mara的内心或是灵魂。
这部电影的镜头其实非常静态,几乎都是观察的视角。
同时,镜头也是主观的,它接近于Mara的主观认知。
当她处于危机中时,电影空间内就呈现了那些错误与不稳定,甚至是灾难。
笑意:嗯,Mara有时也有一些小暴力,比如把咖啡倒在狗身上,或者打死苍蝇,这也反应了她内心的脆弱敏感。
Ramon:对,在这个世界上,时常有一些柔软、温存的时刻,但同时也有暴力与攻击性的时刻。
它就像接近与疏远、温柔与攻击之间的一场舞蹈。
也许Mara希望Lisa留在她身边,不想让她离开,她想保持现状,但她没有哭,她撒谎,刻薄,不肯帮忙把柜子搬下来,有时还具有攻击性。
温柔是拉近距离的方式,攻击性是拉开距离的方式。
当Mara杀死苍蝇的时候,她和Jan的接近瞬间就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又变得非常遥远。
而她把咖啡倒在狗身上,是想让她有种不可预测的感觉。
笑意:人物之间的眼神凝视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强调他们的眼神?
Silvan:在这部电影里,凝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这一点,演员如何注视,眼神有多深切。
就像Ramon说的那样,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人对连结的渴望。
我们想用镜头分开角色们,只对着一个角色拍摄,然后切到另外一个观察这个角色的人。
这些是硬切(hard cuts),它们并不能把人连接起来,而是进一步将他们分开。
整部电影的这种分离架构就突出了这些凝视。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强调凝视,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美。
Ramon:有意思的是,角色有时是主动的,而当他们作为观察者的时候,则是比较被动的。
比如当角色站在门口,看到一个场景之后,这个角色也看到之前发生的情况。
这也增加了不可预知性。
其实那个楼里有很多房间和公寓,有门和墙隔开,但有时候观众会有这样的印象,好像这是一个开放的房子,没有任何墙和门。
门和房间是一种隔离或者禁锢的东西,但有时影片里的角色就好像无处不在一样,你没有听到他们,突然他们就来了,像是鬼魂一样。
这让整个世界变得很通畅,门和墙虽然存在,但没有限制角色的进出。
笑意:我也看了你之前的电影《奇怪的猫咪》。
我觉得有些处理和这部类似,比如静物的蒙太奇,它的作用是什么?
Silvan:有几个作用。
最重要的作用是把电影分成几个章节,这些展示的物体伴随着背景音乐,像是电影中的一个暂停和休息,给观众一些时间去思考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这就像写文章时的标点、换行一样,另起一个新的段落。
另一个作用是,因为我们喜欢实时的叙事,它是按时间顺序的,没有很多省略。
但是当你再把这些之前在场景中作为元素的物体展示出来,比如说,Mara刚刚抽过的香烟,那么整个电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好像是非线性的,尽管在整体来说是非常线性的。
我们喜欢的它给这个世界增加的复杂性。
还有一个作用。
古典叙事只呈现对情节重要的东西,有一个主人公,整个故事和摄影机只是跟着这个人走,一切都被这个情节所驱动。
但我们对这样的叙事很感兴趣:展示、强调一些并非故事中心的物体与角色,这些物体在经典叙事中往往不会得到一个镜头,因为它们被认为不值得被展示,还有其他的人物角色也是这样。
但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叙述者可以左顾右盼,发现各种东西。
其他电影中的叙述者不会这样,因为他们要把很多精力聚集在情节上。
笑意:片中的音乐是如何选择的?
尤其是那首"留声机华尔兹",营造了影片的气氛。
Ramon: “Voyage Voyage”这首歌我们在拍摄前就已经决定了。
因为片中Lisa的母亲和Jurek在拍摄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
华尔兹的话,我们只知道会有电影配乐,但不知道用哪一个。
我们尝试了不同的可能性,有些更有戏剧性,有些太沉重了。
一开始我并不觉得这首华尔兹很合适,但Silvan特别喜爱,他觉得很有趣。
试了一下之后我也喜欢上了,很喜欢它的轻盈,有点喜剧的感觉,也有一些小转折,我们喜欢这种对比。
它让整部电影像一出轻盈的小剧。
派对时播放的“Voyage Voyage” 笑意:还有影片的颜色,有点类似于侯麦电影中的颜色。
Ramon:我们喜欢用三原色,红黄蓝这样的纯色。
有些剧情性比较强的类型片喜欢用偏蓝或者偏绿的色调,有一种颜色主导。
我们不想这样,而是用那些主色调。
侯麦的电影我们很喜欢服装与布景设计,轻盈又多彩。
有点像包豪斯的颜色。
我们希望有一个颜色的冲撞,而不是过于平淡。
笑意:可以谈谈你喜欢哪些导演或者作品吗?
Ramon:很喜欢法国电影,喜欢导演埃里克·侯麦、罗伯特·布列松。
法国的剧情片角色都非常有趣,尤其是女性,经常有很多复杂的角色,我喜欢角色充满神秘感的电影。
意大利电影我也喜欢。
我也很喜欢亚洲电影。
通常来说,暴力经常被用于类型片,特别是惊悚片。
在日本或韩国电影中,血腥暴力元素经常会与精神或者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暴力元素的运用对我来说比类型片更有意思。
笑意:兄弟一起合作拍片的感觉如何?
在前作《奇怪的猫咪》中,Ramon是导演,Silvan是制片人。
Ramon: 在《奇怪的猫咪》中,Silvan不大在片场,而是在制片办公室,这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艺术合作,因为他担任了制片人的角色。
而在《女孩和蜘蛛》这部电影中,我们的艺术合作在写剧本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拍摄过程中,他是副导演;拍摄结束后,他也一直参与后期制作。
所以在这部,我们艺术上的合作更加紧密。
我们将来应该还会沿用这样的合作,有一个亲密的兄弟一起拍电影是不可思议的。
10 ) 《女孩和蜘蛛》:流动的情绪,无声无息
古人云:螺蛳壳里做道场。
若将其用在影视作品中,毫无疑问是一种高超的技巧。
在我近期的观影中,有两部作品堪当此谓:《9号秘事》与《女孩和蜘蛛》,前者关乎叙事的精巧,后者则是情绪的涌动。
前者暂时不表,简单谈一下后者。
作为2021年柏林电影节奇遇单元的获奖作品,你很难不被《女孩和蜘蛛》所折服:一种如诗般的电影质感,一种无时无刻都在弥漫着的情感的流动:冷漠的亲情、妒忌的友情、朦胧的爱情(抑或情欲)。
它有完整的叙事,还有形式感极强的场景转换,甚至一些超现实的描写。
但在我看来,它们都在为情绪服务,这些情绪塑造了人物性格的张力,让你不由得沉浸其中。
而蜘蛛呢,它是爬行者、旁观者,它在人们身上的爬行造成了直接的物理连接,它所织的情绪之网则将所有人束缚其上。
所有人彼此相互联结,每个人情绪的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该怎么评价《女孩和蜘蛛》?
我觉得不需要评价,更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就像电影中不时出现的那曲Eugen Doga的《Gramofon》一样,它就是一首情绪的颂歌,感受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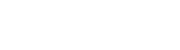


















































不知道在讲啥,不喜欢。。。
取用人的身体与建筑作为容器,承载事件/动作发生过后的形态变化。非常稳固,视线的高度与距离几乎全都是恒定的,与此同时,整部电影中门是消失的,一切都是在面前的。
文本上信息的丰富性看起来能支撑起120分钟电影的体量,声音调度和镜头调度都是出色的,色彩运用得也极大胆。最有意思的是某些近景镜头中,人物的关键性动作(互动)被排斥在景框之外,某种程度上却又加深了凝视感。
胜在镜头和人物神情,也止于细节、困于场景,不是我的菜。
看完穆赫兰道后,本来想找个清新片缓缓,结果这片子让我更晕了🙃
毫无疑问是今年最佳德语电影之一!1.影片精准而微妙地平衡了断裂与流动、日常与设计间的关系,全用固定机位长焦中近景镜头,传统连贯性剪辑中的全远景定场镜头与连贯一致的画面空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持续流淌的声音和人与人之间的凝视形塑出联动贯通的画外空间,一如角色间若即若离、在孤独自在与欲求连接间徘徊摇摆的关系(同样契合于船上女清洁工的诗意自白)。2.限制性镜头与对声音透视的把控颇似布列松,赏心悦目的配色契如侯麦,对另一时空的记忆与梦境的无缝穿插则令人想及雷乃,转场时的空镜蒙太奇极富空无诗意,浸染着小津安二郎之味,而角色举止与环境氛围又很德式。3.搬家的舍离与变移也与片中物件的“熵增美学”相贴合,恰似钻裂的地、四散的羽绒、破裂的杯子与被红酒侵袭的平面图。4.苍蝇与蜘蛛恍如嫉妒与欲望的载体。(9.0/10)
简直费解,也许是翻译有问题。但光看女孩那下一秒就要杀死人的眼神但看了30分钟还是几乎没有进展,来来回回,烦透了
4+1/待重看。 固定机位的拍摄并无沉闷感,运动感由人物不断地出画入画,调度站位突出景深,以及你我彼此游离交错的目光制造而来。很久没有在银幕上感受到如此亲切的时刻:风的呼吸,雨的敲打,阳光的照拂,远处的琴声和角落里的猫,每次转到空镜都会短暂沉迷于那里静谧流淌的诗意。 人物不多,彼此关系却复杂隐晦且暧昧,看似波澜不惊的对话,内里却是波涛汹涌,一次离别正如那把要钻入地心的钻,在所有人心里都留下了裂痕,一切都在摇摆,但永远会有一只海鸥为你独自吟唱
见长评
想起柯西胥的宿命1也是,男主跟女主一样置身事外的局外人视角
剧本很下功夫,视角也好独特。通过对话建立的人物,通过闭合事件和相对密闭的空间织成了一张大网。有趣轻巧。但有点难集中也是真的。
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的空洞无物,整部电影在狭窄的空间里摩肩接踵,给各种特写镜头,但是大人讨厌,孩子讨厌,狗也讨厌,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串起人物的情绪,只能理解为导演的故弄玄虚。
为了风格牺牲了角色的表演,可风格做的不够透,角色也像木偶,女主很耐看。
蛛网般的情感关系,建筑空间内同样错综复杂的来往人际,蛛网被编织,而空间也被人工美学而获得温度,将无机材质转化为有机组织,营造出奇妙的向内的人类微型景观,在捣碎与重建中得到强调。
3.5;通过电影空间的延伸,不断激发着观众的感官。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画外空间的事件,通过声音相互连接(楼下的猫和婴儿的哭声,街道上的电钻)。一些突如其来、自说自话的情绪表演还是有些多余和刻意;总体没什么新鲜的,跟布列松和雷乃相比还是太相形见绌了。
基本没有故事,全是暗流涌动的情绪,无限放大的人与人之间的拉扯,恶意居多,偶尔会心一笑瞬间冰释,但河水下的冰依然在那儿。导演的视听语言很牛逼。PS感觉像在看漫画,因为全是定格。
叙事很特别,要么来自作者的内心感触,要么来自他的细致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有味道,当然这些离不开画面的干净处理。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设计有些刻意,如同全片的景别都是卡着上半身
跟《邂逅在六號車廂》都用了Desireless的Voyage voyage這首歌耶⋯⋯
女孩走了,留下网。所有访客和活动都牵动网,留下破洞和遗迹。
滞重到都有点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