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剧情介绍
这是一个卡拉布里亚岛的小村子,依山傍海,从山麓间,你可以看到远处的伊奥尼亚海。这是一个好似时间停止的地方,这里的石头有权改变事件的发生,而山羊们则会停下来思考天空的由来。 这里住着一个已经时日不多的老牧羊人,他病了,他坚信他找到了续命的良药,他从教堂的地板上收集灰尘,每晚就水喝下。 在一个羊圈里的一小片黑土地上,一只山羊生下了一只小白山羊,生命最初的不适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它的眼睛立刻便睁开了,它的蹄子已经可以支撑身体的重量。整个村子的生活都被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充满了希望。小羊在逐渐成长,它变得强壮起来,开始玩耍。 一次疏忽,它独自离开了在休息的羊群抛开,它在厚厚的植被中迷失了方向,直到精疲力尽,在一株雄伟的杉树下歇脚。 这棵巨大的树随着山间的微风摇摆。时间流逝,季节快速地更替,这棵巨大的杉树失去了枝叶摇摆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机械的轰鸣。 杉树倒在...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我想我是基?anone桑塔纳兄弟追逐野马森林警察也有家朱莉娅第一季不吉波普不笑善恶无赦将爱情进行到底辟邪之咒一床之隔希望今天遇见你母女姐妹淘幻觉之书小女神花铃热血杨家将诺比特这里发现爱绝对占领午睡公主格林第四季末世长安小时代4:灵魂尽头月光变奏曲龙门驿站之蝴蝶飞米奇和朋友们:不给糖就捣蛋我永远爱你主席白夜追凶
《四次》长篇影评
1 ) 观照自己
地球上万事万物,不外乎生老病死,一切都是循环,亿万年来如是。
电影简单朴实的故事,没有对话,用人,羊,树木,木材,所谓的四次,或者灵魂的四次旅行,来反映生物的生死。
哲学的层面,看待万物,看待生死,从而观照自己。
所谓的宗教,古老的巫术,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永恒的话题,也是理不清的。
庄子“箕踞鼓盆而歌”。
死亡是终极的哲学主题。
2 ) 230919:四次
老人衰死,群羊出圈,这是第一次。
小羊迷路,卧死于树,这是第二次。
巨树被伐,装点成仪,这是第三次。
木炭源木,入囱化烟,这是第四次。
唯二的趣味来自第一次的狗取石、车破栅,和第二次的人攀树、众喧腾,两次都是仪式。
第二次或许也是,毕竟羊戴上辔头,有约束的意味。
最后一次,算是最为静而隐晦的仪式了,所有生命都变为焦黑。
所以,以“仪式”的端庄耗尽“生灵”,四次。
3 ) 视觉表达与叙事
这部完全不依托语言对白来表达创作者想法和观点的电影作品,借由宏观与微观镜头的切换,向观众平等的展现了人类与非人类个体的生命轨迹。
影片画面主要是由中远距离镜头和近距离镜头两类组成,其中远镜头主要呈现的是一种疏远、不带感情的观察视角,但这样的视角却又透过细微的镜头移动和转动,传递出一种好奇和关心的态度,仿佛自然正静静地看着牧羊人、小羊、树、木炭在时间里的变迁和兴亡。
而这四个生命、四种生命形态的消长与变迁过程,便构成影片的叙事主线。
沿着这条叙事主线,由于四个生命主体都置身在简单重复的场景和作息之中,展现了一种略显无趣、卑微且不由自主的生命状态。
例如牧羊人年岁已大且身体虚弱,独自过着简单且不算太富裕的生活。
老人每日早晨起来便去放羊,回来后会去小镇送羊奶,顺便去教堂拿‘药粉’。
到了夜晚,他脱去层层外衣、饮下‘药粉’后便就寝。
影片透过固定的场景、固定的镜头位置和角度,呈现出老先生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直到有一天,老人不慎将‘药粉’掉落到野外。
夜晚老人四处找不到它,只好急忙忙地出门去索要新的‘药粉’,但无人开门,老先生最终只能颓然回家。
结果隔天早晨,老先生没能准时起身,不久竟然就在床上断气死去。
这种对于生活的顺从与无力感展现的是一种‘水平超越’:在自然选择和实用主义的框架内,人类所拥有的具有‘特权地位’的思维和意识毫无用处(Goodenough, 2001)。
与此相似的是,小羊的突然走失、大树在茂密森林中被看中并砍伐、木头在节日过后就被人们送去熏烧成为木炭,都给人一种天地无情、生命无常的伤感。
然而在叙事主线之间,是那些不断岔出的近镜头,当这些镜头扫向这四个叙事主体之外,关注的是容易被忽视的非人类个体的运动,它们都和人类一样被完整地记录在影片中。
例如老先生在草丛中排便后匆忙离去,镜头突然带向那个草丛,画面中出现了那个被老先生掉落的草药粉纸袋,但除了这纸袋外,还有一大群忙碌地赶来搬运纸袋的虫蚁。
而当老先生隔夜卧病在床、未能起身时,牧羊狗跑到路上朝着村里办活动的人群吠叫,害得他们在匆忙间忘记拉上货车的手刹,结果货车撞破羊群的围篱,羊四处乱跑,其中更有些羊跑到老先生家里,将他盛放浆果的锅给撞下桌子。
这些来回切换和延伸的微观视角,呈现出的是天地间的生生不息,是超脱个体与短暂生命的‘万物有灵论’,导演试图传达:生命意义无差别地存在于每一个瞬间和每一个事物里。
同时,影片中的镜头视角的视觉表达也同样充满象征寓意,导演在视觉上将人类和非人类个体并置比较。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观看视角:分别是火化老人和焚烧木炭。
火葬老人是的镜头是从老人所躺墓穴的内部向外看去,门被重重关上,整个屏幕变黑成为一个巧妙的转场。
第二次焚烧木炭也有一个镜头是由堆放的木材内部向外看去,观众的视线逐渐被人搭上来的木材所遮挡,画面再次由明亮变为黑暗。
从前后两次焚烧能够看出两个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联系:村民们用火葬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尸体,由此展开第一次轮回。
第三次轮回中树木即将转变为木炭,也是通过用火焚烧的方式才能完成转变。
人类的消亡以及树木的消亡在影片中被放置在同一镜头语言和叙事情节中,不难联想到这是导演对于人类中心论的抵抗。
纵观整部电影,其叙事描绘的是生命的轮回,而人类(牧羊老人)只是轮回中的组成部分而并非故事中心。
具体表现为一种生命形式按时间顺序取代另一种生命形式(Seger, 2014)。
剧情中牧羊老人日复一日过着平凡而平静的生活,如果不是羊跑出了羊圈并有几只聚集在老人床榻前,村民不会发现老人已经死在自己的家中。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镜头采用了老人临终时模糊的视线为视角,与羊的对视,展现了电影的轮回主题。
老人死了,同时,一只小羊出生了。
小羊挣扎着去适应(或者说重新适应)地面上的生活。
此后的某天,小羊在树林里迷了路,它蜷缩在树下,黑夜将它们一并吞噬了。
虽然没有明确的展示小羊是否死亡,但是之后镜头中出现的白雪以及电影对于轮回的强调暗示了小羊已经死去。
羊和树的依偎又一次完成了灵魂的接力,树在镜头中做为自然界灵的下一个主角。
接下来,人们在春天砍伐了树放到村中央作为某种节日的庆祝仪式。
节日过后,人们把树砍倒,之后把树运到村外,和其他的树一并烧制成木炭。
影片的最后,卡车拉着木炭回到村内,车上的男人把木炭分给各家各户。
电影里所呈现的四段不同的生命经历,传达的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中的四段故事。
此外,轮回也不仅仅是四次生命的轮回,也是电影开头和结尾两次焚烧木炭的镜头相接所形成的环状结构:第一次焚烧象征轮回开始,但第二次焚烧并不是象征轮回的终结,相反,轮回似乎永无终结。
由第二次焚烧开始,随着卡车运回村庄,也使那一个灵魂回到故土,故事重新开始,也可以看做是回到开头。
无论是哪种观点,整个电影的头和尾都正式相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观众能够从叙事中意识到,人类并不处于自然以及电影世界观的中心框架中(羊,树和木炭也没有占主要地位),他(牧羊人)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一种,轮回中的一环。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道教对于‘世界运行’这一方面的哲学观点,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Heaven and earth aren't humane’:这句话暗示着以“heaven and earth”为代表的自然世界,不具备像人类一样的品质,比如同情或道德。
在道教中,宇宙按照其固有的原则运行,这对人类的价值观和关注点来说似乎是冷漠或不可理解的。
这个概念鼓励个人接受宇宙固有的非人类的本质,并使自己与宇宙的流动保持一致,而不是试图将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想强加于宇宙。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straw dogs’这句话中,‘ten thousand things’是道家的说法,指的是世界上无数的形式和现象。
“straw dogs”是中国古代用于仪式的物品,在仪式中受到尊敬,但之后被丢弃和践踏。
这句话的内涵是世界上存在无数的形式和对象,尽管它们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最终在存在的宏伟计划中都是短暂的和无关紧要的。
在道教中,这种观点提醒人们物质现象的无常和微不足道。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自然世界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一切只能顺其自然的发展。
通过结合道教以及电影中的叙事,‘轮回’的剧情设计有效的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导演意在向观众呈现一个超越人类个体为中心的自然世界观。
4 ) 是来处,也是去处
尘:是信仰的良药,是未被原谅的过往,是被舐犊的爱,是盘根下混杂的泥,是被切割时的木屑,也是那燃烧殆尽后的尘土。
黑白:是黑蚁在白须间的游历,待归盼来的忠犬,是教堂门前的黑影,是与生俱来的斑点,是白雪皑皑中的屹立,是布袋里的黑体,也是交替的昼夜。
自由:是被羊顶翻的铁锅,是被汽车撞坏的栅栏,是不再出声的挣扎,是被套牢的龙头,是水渠前的怯懦,是四天般的四季,是被剥光的茂密,是被熏烤的土窑,也是那一缕屋顶上飘出的青烟。
水:是混入了浑浊前的清澈,是哺育生命的奶水,是干枯后的陷阱,是长青的痕迹,是被火焰带走的氧气,也是那环绕着山头的云雾。
森林:是喂食羊群的草地,是途间小憩的拱廊,是炎热之处的树影,是装着离别的木棺,是历练成长的木桩,是迷亡林间的枯枝,是安心依靠的大树,是周而复始的寂静,是祭奠之时的欢愉,是家家户户的温暖,也是那密林间的众相。
我迷失于衰老,迷失于路途,迷失于岁月,迷失于思变也重生于清澈,重生于雪白,重生于赤裸,重生于光明我既不是火光,又仍为火光我即茫然无知,又为生命引导我是那千万之中的一个,也是千千与万万是来处,也是去处。
5 ) 万物皆灵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岛的一座村庄。
电影的四个故事分别围绕不同的主角:一位病危的老牧羊人,一只刚出生的山羊,一颗巨大的杉树和一堆木炭,用诗意的影像描绘了生活和自然的联系。
电影完全没有用到任何配乐,对话和视觉特效。
自然景观,环境音和非专业演员的运用让这部电影在形式上趋近于纪录片,但是独特的镜头语言让它在现实主义的形式框架下独具一番魔幻的色彩。
影片中四个不同种类,不同阶段的灵魂相互叠加,转述了一个哲学式的现实寓言。
毕达哥拉斯 ‘灵魂论’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主张灵魂不朽和转世轮回的思想。
他认为灵魂死后摆脱躯体还可以继续存在并达到完全的和谐与自由。
经过一定的周期,灵魂会再次投生到新的躯体(人或其他生物),继续另一个轮回的生命。
《四次》的主题基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论”。
灵魂在四种生命形态-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之间反复循环,经历死亡和重生。
“灵魂论“的思想贯穿了电影的主线,将看似无关的四个故事链接在一起:老牧羊人的死承接了小山羊的出生,小山羊走失羊群后死在杉树下,将灵魂传递给了杉树,杉树被人类砍伐后其灵魂化作煤炭。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村庄烧煤升起炊烟,暗示灵魂经过四次传递又回到了人类的躯体。
除此之外,毕达哥拉斯还主张灵魂的平等,即万物的灵魂在自然中承载着相同的分量。
他的主张与人类中心主义论对立。
在《四次》中,这种主张通过灵魂所附着的四个躯体在影片中所承担的相等的主体性表现了出来。
导演通过视点的切换,让动物,植物和矿物担任了不同故事中的主角,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电影中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方式,给自然的元素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让动植物和非生命之物有着与人类相同的尊严。
镜头语言与叙事方式《四次》是一部不依赖传统剧情片叙事和好莱坞式视听技巧的电影。
它通过不同景别,镜头移动,主客的镜头视点切换,让非人为的元素参与到叙事当中。
*镜头的重复*“同样是拍一架飞机,好莱坞会让这架飞机飞过,扔下炸弹并被击落,但是在意大利电影中,这架飞机在同一片天空飞过一次,两次,三次。
” 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探究的是生活在重复中浮现出的真理,而摈弃了对生活“意外性”的具体描述。
现实主义对真理的探究方法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传承。
这个镜头在第一个故事中重复出现了八九次,以此来反应人物生活的重复性但是电影在重复的记录中隐含了寓言式的叙事。
在这个村口的镜头出现的第七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牧羊犬拨开石头让卡车冲破羊圈这个非常规事件打破了现实的常规,暗示了牧羊人生命的终结,标志了山羊成为牧羊人灵魂继承者的转折点。
* 象征性元素的重复*这部影片非语言化的叙事关键,不仅在于利用重复的镜头,还在于利用重复的象征性元素。
相同的元素在不同故事中重复出现,被赋予表意之外的指涉意义。
故事1和故事3中的牧羊犬
牧羊人脸上和杉树干上的蚂蚁
故事1和故事4中 同一户人家在购买煤炭与自然和生活相关的种种元素看似偶然地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实则被作者赋予了指意,暗示了万物灵魂的相互纠葛,使四个看似绝望的故事暗藏轮回的希望。
巧合被制造,平淡而重复的现实被赋予意外性和荒诞感,这是对现实主义的改良,也是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精神向真理跨进的方式。
*非人物的主观视点*主观视点的运用让非人物的角色“说话”,通过镜头给生物,甚至无生命之物赋予了意志,呼应了“万物有灵”这一电影的核心概念。
杉树干做前景 眼看着自己走向毁灭
小山羊的主观视角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安东尼奥尼曾在文章中表述 “景观也可以成为影片主要角色”。
《四次》印证了安东尼奥尼的主张,让自然成为其本身的叙述者,并通过摄影机完美地呈现了这一意图。
波河上的人 (1947)7.51947 / 意大利 / 纪录片 短片 /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安东尼奥尼1947年影片Gente del Po - 以自然景观(river Po)作为电影主角现实与宗教许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都融入了宗教的元素,并由此提出“宗教信仰能否救赎现实的苦难”这一哲学性的开放式问题。
经典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 主角和儿子闯入正在礼拜的教堂,儿子误将神父认成贩脏者,掀开了忏悔室的幕帘。
极为讽刺的一幕暗示了作者对宗教消极的审视在电影中,老牧羊人将教堂的灰尘当作药材,但最终未能被信仰治愈。
他没有遇见神迹,被基督救赎,但是在电影营造出的“灵魂论”现实中,他的灵魂得到转世,并在动物的躯体上获得重生。
在新现实主义时期,以探究自然真理为核心的电影避不开对宗教和现实问题的权衡。
宗教,作为意大利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新现实主义电影中被重新考察,不同作者的态度影响了宗教在现实中的权重。
《四次》作为新现实主义的沿袭,也切入了对宗教的思考,但其导向不是天主教-灵与肉一同诞生和死亡-的观念,而是灵魂与肉体分离并实现自主的循环和重生。
6 ) 圈
尘归尘,土归土,所有事物绕一圈最终又回到原点。
迟暮的牧羊人靠着用羊奶换来的教堂的灰尘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撞破的栅栏是巧合也是注定。
新出生的小羊羔还没来及好好看这个世界,就在荒野中死去。
树在漫漫时光后,在庆典中轰然倒下,烤的漆黑的木炭在火中燃烧,谁家的烟筒冒着浓浓的烟。
一切物质都在轮回,在那个宁静的村庄里体现生命最简单的秘密。
7 ) 《四時之樂》的「生成自然」
意大利電影《四時之樂》(Le Quattro Volte)由米切朗基羅.法爾瑪提諾(Michelangelo Frammartino)執導,四段故事組成,中文的副題「人.羊.樹.煤」給予觀眾明確的指示,這電影包含四段故事,而主角分別就是人、羊、樹和煤(其實是木炭)。
人、羊、樹和木炭驟眼看來不相干,導演卻以別具一格的電影手法把他/牠/它們串連起來。
當然,羊、樹和炭的串連比較有跡可尋,可以看作是物質的轉換︰羊在山野中迷路,最後無聲無息在雪地中消失(大概是在大樹旁死了);冬去春來,小羊大概腐化,成為養份,變成樹的一部份。
這時小鎮中的人到山野把樹砍去,用以慶祝他們的節期;最後樹被鋸成小塊,送往工地燒製木炭,而炭又再次運回小鎮,供鎮民使用。
我們完全可以以物質的轉換去理解羊、樹和炭的關係,然而人與羊的關連就顯得比較特異。
故事是以「人」開首,老人在小鎮中以牧羊維生,每天帶羊到山上吃草,以羊奶到教堂換取灰粉,晚上把粉沖水喝了,以解救他不停咳嗽之苦。
一天他不慎把粉留在山野中,那天晚上就在自己的床上死去。
鏡頭一轉是母羊產子,這轉折像是告訴觀眾,小羊就是老人的「轉世」(reincarnation)。
當然,我們可以以生態學的角度去思考,說老人被埋在土裡成為養份,滋養小草,羊媽又把草吃掉變成養份,供養肚裡的小羊。
但電影中的教堂和基督宗教儀式,牧羊人與羊的設定,實在很難不叫人去得出這形而上的抽象關連。
然而,基督教裡是沒有「轉世」這觀念的,有的只有「道成肉身」的「入世」(incarnation)。
導演巧妙的轉換揭示出他生態意識所在。
無可置疑,電影的後三部份導演表達出人與自然在物質層面上是如何相互聯繫(interconnected)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
人固然也是物質,我們也可以以上述觀點去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但我們很難把人單單約化為物質,而忽略在西方文明中發展出來關於人類「超物質」(如靈魂)的思想傳統。
面對基督教神學的傳統,導演以「人轉世成羊」與「神道成人」作類比,折射出生態神學的思想︰人可能是高於自然,但同是也是自然,正如基督耶穌是高於人的神,但同時也是人。
觀眾看到主要角色人、羊、樹和炭,除了是因為導演分場所致,也因為中文副題的引導。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主角」貫穿整部電影,那就是水。
電影在訴說牧羊人的故事前,有一段空鏡頭拍燒製木炭的過程──也是片末製炭的過程──而最後一組鏡頭就停在製炭的小丘上氣孔噴出來的水蒸氣。
這水氣不單只是在炭丘上出現,也瀰漫在整部電影和整個自然界中。
這水氣,彷彿就成了「人的靈魂」的轉喻,同時成為生態神學中「上帝的靈」的隱喻︰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啟動創世的程序,並且一直瀰漫在地球的自然歷史中,保有世界,推動歷史。
另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全片沒有對白,就是說,影片只有聲音,沒有構成對人類有意義的「語言」。
這當然是導演在手法上的實驗,接回默片的表意系統,單讓畫面「說話」,讓觀眾更聚焦在畫面上。
另一方面,這手法在電影的主題上,達到了另外兩層的效果。
先是讓觀眾感受,自然界的聲音是可以跳過語言表意系統,直接震盪人的情感的。
就像小羊剛出生掙扎著要站起來的片段,畫面是小羊不斷的嘗試站起來,而聲音則是小羊一聲又一聲高音調的叫聲。
觀眾從此就能體會到自然界痛苦求存的實在。
其次,語言向來是人禽之別其中之一分界,因為人類有語言,所以人有歷史和文化,而西方哲學也以此來區別人與動物。
但電影把人的語言拿走,老牧人只有一把發出咳聲的聲線,與羊發出羊叫沒兩樣,導演以此把人化為萬物中的一種物種。
而在電影最初和最後出現的炭,就成為人的語言的代替品。
炭與羊和樹之不同在於,炭是人以「技術」從樹木(並草和其他物料)中把它「生」出來的,這恰恰可以成為電影的隱喻︰導演以技術從小鎮與自然中把電影「生」出來。
若然這是導演認為電影該佔的位置,那麼這戲最後的鏡頭就顯得耐人尋味。
貨車把木炭運到鎮裡,工人把它們分發到鎮民家中,然後我們看到,屋頂的煙囪冒出一縷白煙︰木炭化成了水氣,回到大自然裡去。
若然木炭是電影的隱喻,那麼導演期待,觀眾在消費(consume)電影後,能「生」出「靈性」來,回到大自然裡去;這「靈性」,不屬於觀眾(鎮民),也不屬於電影(木炭),而是在他們相互接觸的消費(焚燒)中「生」出來。
8 ) 《灵魂的四段旅程》静默中,生命绽放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
”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灵魂的四段旅程》是2010年的一部意大利电影,是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法尔马提诺的第二部剧情长片。
不过,“剧情长片”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太精准,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灵魂的四段旅程》没有剧情、也没有对白,单纯由四组看似独立的观察影片组成,更像是一部短片集或是纪录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部片子又剧情丰满、对白丰富,讲述一段生机盎然的生命故事--这种矛盾的理解结果,其实正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出色的地方。
有人将《灵魂的四段旅程》称为意大利版的《生命之树》,但我个人觉得,《灵魂的四段旅程》透过更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更为朴素和更为开阔的生命观,无论是在意境上还是手法上,都比《生命之树》这部获得戛纳影展金棕奖的作品更显出色。
■内容与视角《灵魂的四段旅程》的内容很简单,先是一个住在乡村的老先生每日靠放羊和出售羊奶为生,老先生在死去后,一只小白羊哇哇坠地、来到人间。
这只小白羊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从羊群中走失,开始在森林里独自徘徊。
春去冬来之间,小白羊栖息到一棵大树底下并终结生命于此。
这棵大树后来被村里的人砍下,运到村里作为祭典活动之用。
祭典之后,大树就被人们砍成木头运到木头堆积场。
这些木头后来又被拿去熏烧成为木炭,烧成的木炭则被分送到村里的各家各户。
如果从人的视角、从一般剧情片的角度来观看这部影片,可能既看不到完整的剧情、也看不到可以感动或思考的故事。
但是如果从“生命”的角度切入,便立即能产生非常具体的体悟。
有人说,《灵魂的四段旅程》是基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论。
毕达哥拉斯派主张,人是有灵魂的,而且灵魂会轮回转世,在人、动物、植物、矿物这四种生命形态中循环重生。
但我认为,《灵魂的四段旅程》虽然以这一灵魂论为基础,以生命的四种形态来看待万物,但在理解和诠释上则不限制在简单的灵魂转世上头,内容中所涉及的四段旅程,更可以看做各自独立的生命历程,从天地的视角来感受万物生命的消长。
■镜头语言与叙事方式虽然说《灵魂的四段旅程》是以“天地万物”如此宏观的视角来观察生命的起灭,但这部影片完全没有落入宗教式崇高、但却又狭隘的精神感召与呐喊。
这部完全不依托语言对白来表达创作者想法和观点的作品,完全借由宏观与微观镜头的切换,借由叙事主线与支线的隐微交错,让生命本身来感动生命。
影片画面主要是由中远距离镜头和近距离镜头两类组成,其中远镜头主要呈现的是一种疏远、不带感情的观察视角,但这样的视角却又透过细微的镜头移动和转动,传递出一种好奇和关心的态度,仿佛天与地正静静地看着老先生、小白羊、大树、木炭在时间长河里的变迁。
而这四个生命、四种生命形态的消长与变迁过程,便构成影片的叙事主线。
沿着这条叙事主线,由于四个生命主体都置身在简单重复的场景和作息之中,隐隐间给人一种无趣、卑微且不由自主的生命状态。
例如老先生年岁已大且身体虚弱,独自过着简单甚至贫困生活。
老先生每日早晨起来便去放羊,回来后会去村里送羊奶,顺便去附近的人家领取一种草药粉。
再次返家之后,他会将捡拾来的浆果放在锅子里。
到了夜晚,他脱去层层外衣、饮下草药粉后便就寝。
影片透过固定的场景、固定的镜头位置和角度,呈现出老先生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直到有一天,老先生在放羊的时候到草丛中排便,不慎将草药粉给掉落。
夜晚就寝时,老先生四处找不着这草药粉,只好急忙忙地出门去索要新的药粉,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入睡、无人应门,老先生最终只能颓然回家。
结果隔天早晨,老先生没能准时起身,不久竟然就在床上断气死去。
与此相似的是,小白羊的突然走失、大树在茂密森林中被看中并砍伐、木头被人们送去熏烧成为木炭,都给人一种天地无情、生命无常的伤感。
这便如同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然而在叙事主线之间,是那些不断岔出的近镜头,当这些镜头扫向这四个叙事主体之外,看进不为人知的世界时,却突然给人一种生命的感动。
就像老先生在草丛中排便后匆忙离去,镜头突然带向那个草丛,画面中出现了那个被老先生掉落的草药粉纸袋,但除了这纸袋外,还有一大群忙碌地赶来搬运纸袋的虫蚁。
而当老先生隔夜卧病在床、未能起身时,牧羊狗儿跑到路上朝着村里办活动的人群吠叫,害得他们在匆忙间忘记拉上货车的手刹,结果货车撞破羊群的围篱,羊儿四处乱跑,其中更有些羊儿跑到老先生家里,将他盛放浆果、悉心捆绑以防虫蚁偷吃的锅子给撞下桌子。
这一切一切来回切换和延伸的微观视角,呈现出的是天地间的生生不息与福祸相依,是超脱个体与短暂生命的宽阔胸襟,是“佛纳须弥于芥子、于芥子中现大千世界”的世界万象。
从个别生命的角度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此生成就了些什么、在于此生得到了些什么,而这一切往往必须待到盖棺时方能论定。
如果在即将离去之时,人生总体是丰衣足食且幸福安乐,并且,或是积攒了财富、或是成就了功名、或是子孙绵延,则可说生命有所意义,否则便是虚度生命的人。
然而,在广阔的天地间、在悠悠的岁月长河里,生命意义无差别地存在于每一个瞬间和每一个事物里头。
■生命的意义在人们眼中看来,老先生的生命卑微且无意义,而他掉落草药粉更是不幸,造成他的生命嘎然终止、荒诞而逝,然而在天地岁月的眼中,因为老先生牧羊,村人们才得以获得羊奶滋养身体,老先生掉落的草药粉和浆果,则生养了更多生命。
至于之后小白羊的走失,虽然没能因此安养天年、产乳给予,但牠的身体却又生养了大树和无数寄生在树上的生命,而大树的被砍伐和熏烧却也成就不同的生养。
这正如《新约圣经》上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
自古以来,“生命的意义”便是人们汲汲营营、不懈探讨的议题,无数哲学家都想找出人生在世、生来死去的目的所在,想由此总结出正确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更由此衍生出种种神学,提出来生和灵魂的概念,以解脱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虚无。
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思想和各种神学思想,《灵魂的四段灵魂》采取老庄式的宏观生命观,跳出以“个人”、乃至于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从天地的角度、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观察和体现生命的意义。
《灵魂的四段旅程》全片都在自然光下拍摄、没有任何对白和配乐,时时回荡耳边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老先生身上的铃铛声、牧羊狗儿的汪汪叫和小白羊的咩咩叫,整体色彩和调性是自然、美好且祥和,有人用“诗意的镜头”来描述,不过因为这几个字不仅概念模糊且已经被用滥,不如就简单地说是影片里头人事物的宁静与不做作、森林田野的开阔、各式景致里头饱和且自然的明艳色彩、以及镜头与画面那不疾不徐的推进和切换速度,给人一种内心澄净和放松的感受,完美地呼应影片的宽宏主旨和超然氛围。
在这样一部没有语言对白、没有配乐、没有灯光操作的作品中,镜头是导演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唯一语言形式。
影片中,除了老先生和小白羊这种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生命形式外,还涉及大树和木炭这种不为人熟悉的生命状态,因此,如何形成顺畅的叙事节奏、如何以有形的事物来传递无形的生死概念,需要非常出色的镜头语言功力才能达成。
影片中,充分利用重复和联想手法来进行表述,让人从具象中理解抽象、从“可理解”中理解“不可理解”。
例如透过众多虫蚁在大树上积极忙碌的单一近镜头,便传递出小白羊的死去和大树的生机勃发。
例如用盖棺动作及其后的黑屏来呈现老先生的死去,而当同样的手法出现在木头被送进去熏烧时,大树的生命终结便赋予了联想后的理解。
这种透过相似性来理解万事万物的方式,除了是一种镜头语言、一种叙事手法外,恰恰也是一种推己及人、同情和包容的处世态度。
其实,《灵魂的四段旅程》并没有为“生命的意义”这一永恒命题给出答案,但它却给出一种看待生命的方式和态度。
相比于《生命之树》里头那种基督教式、有偏向性的“信我者、得永生”,《灵魂的四段旅程》予人的是更为开阔的胸襟,如同老庄思想一般地提示着,人们眼中看到的幸与不幸、生与死,都只是天地运行的一部分,幸与生有其意义,不幸与死也有其意义,而这样的意义却又只是一种短暂的和相对的概念,既不是永恒不变、更不是颠扑不破。
若要深究,个体的生命或许没有绝对性的意义,但“生命的意义”又何尝不是一个无意义的提问?
豁达和超然,用心感受生命,或许比苦苦追求生命的意义更有意义。
9 ) 乱语《四次》(1)——消失的摄影机
这或许是电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摄影机的电影,同时也可以看成第一部,如果我们相信这位名叫弗兰马汀诺(甚至还不怎么名见经传)的意大利导演仍然饱有旺盛的创造力,同时具有改写电影史的野心。
电影史从未缺少企图让摄影机消失的导演,却没有一位曾经真正做到。
比如在费里尼的电影中,方法是不断地加重影像的繁杂度,运用无从捉摸的镜头处理,用巴洛克式影像不断轰击观众感官以达到崩溃效果,观众来不及意识到摄影机存在便被影像裹挟而去。
但这是一种障眼法,摄影机只是在观影中逃脱了意识,却没有被真正消灭。
又比如小津安二郎,独辟蹊径地使用低角度摄影机位,以此来消除导演意识的介入,以一个全知的视角模拟超脱者的视角,但其固定镜头间的剪辑手法依然有着明显“切”痕。
究其原因,是因为摄影机永远都不会“被消失”,而只会“自我消失”。
这就如同欲望,永远无法借由压抑来将其消灭,只能经由我们对欲望的彻底觉知(认清了所有的欲望组成),才会自行消失。
弗兰马汀诺或许是第一位认识到此点的导演,并将这一理念完美落实,从而创造出这部名叫《四次》的杰作。
我们应当感慨是一位意大利人发现了这份原本属于东方世界的秘密,同时作为后人也应当汗颜,我们如此彻底地将其忽视恰恰是因为它深刻地裹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因为一切都太过熟悉了。
上个世纪,一位来自印度的圣人将这份遗产从远古带回现代,这位超然的觉知者最振聋发聩的话语之一是“观察者即被观察者”,弗兰马汀诺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在电影中将这一观念完美契行,从而让摄影机自行消失。
于是,我们可以来谈谈《四次》是如何做到将摄影机消失。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电影里仅仅出现的两处主观镜头,它们的主体都不是人,而是羊。
第一处主观镜头由两个画面组成:前一画面是一只羊仰望天空,紧接着就是飘着云彩的蓝天。
为什么全片只有羊的主观镜头?
这值得深思;为什么电影从头到尾只出现老人的正脸特写?
同样值得深思。
我们可以作出的解释如下:主观镜头一旦是人发出了,观众也就意识到一个观察者,即观众自己;但如果镜头是来自动物的视角,观众就不再有自己是观察者的意识,代入感自行消失。
这就是这部电影带予观众的奇妙观感:无法被以往任何观影经验所污染,它是纯粹、再生的:是自然万象自己叠印于胶片之上,像是浑然天成的上帝之作。
因而,摄影机不再模拟人的眼睛,而是动物的眼睛(羊),甚至可以看成是物质(碳)和一个不再有思维能力的老人(仅剩感知)。
对于动物来说,观察者这一词汇本身即不存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分离纯属基于人类的话语之谈。
只有当摄影机在模拟人(有观察能力的人)的眼睛之时,它才无法被消失,它时刻观察被观察者。
但是,一旦摄影机模拟动物(或物质)的观察,也就只有观察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浑然一体,无谈分离。
正是于这种非人类(更准确说,非人类经验)的观察视角中,人类所有的观察经验自行消失,所有观众都在观影中恍惚间唤回原初动物之本性,我们生成-动物,以一只动物的眼睛观察眼前展开的一切,这些景象不再能唤起我们于生活中积累下的经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作身体的移动:换不起我们的同情;羊群的骚动:换不起我们驱赶的欲望等等——我们即是他们的一部分,观察者消失了,只有纯然的观察。
于是乎,电影成了对人类存在之前的原始窥视,那时一切都遵从着万物本性,在宇宙和谐奥秘中活动。
就是以这般简单又极端的手法,弗兰马汀诺创造性地让摄影机自行消失,从而创造出空间-影像的典范。
他的方法很简单:给予摄影机生命,让它全然地觉知。
于是乎,我们也就明白费里尼和小津安二郎失败的真正原因。
只有到弗兰马汀诺的手下,主客体间的界限被打破:只余观察,不再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分离;只有电影,而不再有摄影机与被摄录画面的分离。
这两者本质为一,它们以绝然清澈的视角自现于这个世界。
注:“观察者即被观察者”,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之一。
照我个人理解的深意是:彻底全然的觉知可以把人类从时间的深渊中解救,人类内心所有的痛苦均可以归结为“我”,当时间不在,“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消失了,主体消失了,只客体留存,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心理问题的产生与作用都在一个对象上,就好比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施在同一物体上,它不会有任何变化。
克里希那穆提的这句话可以终结全人类的痛苦,不是靠信仰,靠的是人类自性之光。
只可惜,到现在人类依然活在自我痛苦的深渊里,他没意识到这份痛苦的根本来源正是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作了分离。
10 ) 一棵树
夜晚,阳台,晚风,早秋沙沙作响的叶子。
一部四季轮回的故事,无对白的电影。
我曾经邀请一个人死后一起树葬,埋在一棵柠檬树下,或者任何一棵我们想变成的树木。
那样就可以以另一种形式感受风,以另一种方式看云,以另一种方式交谈…比起一棵树,我们太过孤独了。
以前时间的流逝是美好的,是遵从大自然指示的,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我们春耕秋收,生老病死。
与自然交流,用自然定义时间,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这些诗意的节气指导我们的行动,自然就是最伟大的神灵。
如今呢?
时间是怎样的。
我们睡眠时间是工作时间的空隙,吃饭时间是工作时间的空隙。
交流的时间以自我此刻时间为标准定义为一小时前,三天前,半年前,一年前。
我们不耕种,不期待,我们活着。
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孤岛化,忙着交友,却不交心,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如果内核是空虚的,灵魂的种子如何发芽扎根呢?
前两天,又和朋友谈到永生,如果可以永生,那跟死了有何区别。
万事万物没有消亡就没有新生。
没有死去的恐惧就没有活着的美好。
我愿意成为一棵树,一只白羊,一个牧羊人或者别的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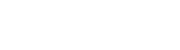





























羊的铃铛声格外脆耳。
七十多分钟,时间不长,没有对白,大自然很美,喜欢小山羊和树的两段。也知道了木炭是怎么制作的,算是收获之一。
过于哲学,看完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的哲思。
真适合无所事事的周日夜。小山羊超搞笑超萌~
有灵无感
生活的真谛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吗?我实在附会不来,这不是电影。我只想说一句,什么鬼……
这种片4星打得很坚挺。
风物诗 好像云南啊……山区果然都好像
一种纯粹影像:取消紧凑叙事与戏剧冲突,非职业演员与动物的自然演出,无台词,无配乐,自然光,一切都在客观冷静的镜头与多层次的同期自然声中缓缓流泻,轮转,兴替,一如毕达哥拉斯的生命四循环论。| 室内镜头似[撒旦探戈];白烟与尘埃首尾相衔,蜗牛锅,冲破羊圈的卡车,羔羊分娩,蚂蚁。(9.5/10)
无聊 我们村庄稼水草生生不息 绵羊耕牛扎堆成群 榆树槐树高过屋顶 男童女娃窜来跑去 可谓是到处生机 建议来给我们干农活 比装着被电影憋出诗意更高级
太文艺了。。。分给形式吧
第一次看非紀錄片的無臺詞電影,怎麽說呢,比想象中有趣。大量固定的長鏡頭,以緩慢的步調記錄下生活,充滿寧靜祥和。四次,四种生命,隨著時間延續,命運交曡。不過還是得說,不適合犯睏的時候看……或者也可以說很適合-v-
虽然摄影剪辑都很好,但不得不承认,是鄙人境界低了。
平和。
这不就是生死疲劳吗
单调的画面,简单的人物,几乎无声(偶尔有羊咩咩叫,狗汪汪几声),尚未看懂导演表达的意思,但看到老人发现落下教堂拿到来治病的“香灰”时着急无助的样子,感觉有种凄凉。
万物皆有灵
用鏡頭說故事的典範。前緣方盡,後緣初起,生生不息,無斷無續。
不懂
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羊、树,被导演赋予了似有似无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