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摄像机》剧情介绍
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丹尼尔·奥特尤尔 Daniel Auteuil 饰)与妻子安娜(朱丽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 饰)、儿子皮埃尔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被乔治从家门口捡来的录像带打破,这盒录像带显示有人静静地注视着乔治家的一举一动。很快,更多的录像带 和恐吓性质的明信片寄到了乔治及家人手上。乔治对看不见的敌人殊为紧张,开始小心保护儿子,并且为录像带的内容指引,回想起多年以前,差点成为母亲养子的阿尔及利亚遗孤马吉德。乔治怀疑录像带的始作俑者即为马吉德,于是登门拜访,却引发了意外的结局…… 本片获2005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费比西奖等二十余项专业褒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扑通扑通我的人生局外人芭比和肯德拉闯入乔·鲍勃汽车影院狂欢圆形图金色时光神奇女侠新生化危机拜托了!大侠金银花开图书馆员:下一章第一季红衣醉ALDNOAH.ZERO第二季亲爱的司丞大人嫌疑之下第二季剑归何处做爱做的梦侠义神捕之边城迷案品酒要在成为夫妻后薄冰上的舞蹈薰香花朵凛然绽放铁塔油花浪漫曲主宰这座城暗夜情报员第一季人造天堂诱捕正义敏感事件最后一镖四月一日灵异事件簿风中的女王第一季赢家先生第一季
《隐藏摄像机》长篇影评
1 ) 隐藏的仇恨,隐藏的危机。
这部电影看到最后,我觉得谁是隐藏在摄相机后的人早已不在重要,重要的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的愤懑,彷徨、仇恨都一览无余,而且潜藏在这些愤懑、彷徨、仇恨之后的危机也昭然若揭。
男主角Georges在幼年时候对Majid所做的一切,不仅改变了Majid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更是因为对Majid会因此而报复所产生的怀疑和轻蔑,导致Majid当着他的面割喉自尽。
这个结局给Georges带来了永久的痛苦和内疚,并让他和妻儿的生活也从此蒙上了比以往更大的阴影。
可以说这一切的悲剧,都起源于Georges从孩童时代对身为阿尔及利亚人Majid的猜疑和蔑视。
这是Georges一手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个人之间的种族主义情绪,放大到国家来说,不正是法国警察在1961年对阿尔及利亚平民示威者的屠杀,以及911事件及其后整个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仇恨的写照吗?
导演是不是在暗示着,这种隐藏在西方国家中对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是否也向剧中主人公那样,会带来以后更大的悲剧,并让心怀仇恨的人一辈子在内疚和痛苦中渡过呢?
剧中的摄像机我觉得可以不用理解成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或许也根本没有一个躲在摄像机后的人。
这一切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说悬点儿,三尺之上,必有神明。
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内心里,总有这么一架摄像机在注视。
影片的最后一幕是Georges的儿子学校门口学生放学的场景。
我看到人群中,Majid的儿子走上去和Georges的儿子在交谈,然后两人相继离去,这时全片落幕。
我想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谈话给观众留下了足够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他们在说些什么呢?
是在下一代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还是互相之间得到了谅解呢?
不得而知。
但最起码,两个人之间,两个世界之间开始沟通、对话了。
2 ) COM263 Film Blog_Caché
“Television accelerates experience, but one needs time to understand what one sees, which the current media disallows. Not just understand on an intellectual level, but emotionally.” —— Michael Haneke Michael Haneke is one of the famous Austrian directors, his films often use media as the means that is similar with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to social construction, reflecting the post-modern society of the middle class filled with media violence and void caused by material piling. Television a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dium, it uses anthropogenic editing visually and auditorily accelerates the experience subject’s presence. However, the real happening only exists in one place,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using medium as physical object to create countless simulacrum of reality with a compressed time. In the interview of Haneke, he mentioned about the danger of media several times, especially the violent moving-images included in television.
It seems easy for audiences only watch the image and take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media, but it hardly can create an empathy and replace the real presence in real time and space. It the constantly played videos that shows violence and pain in distance on television leaves a vague feeling of guilty and incompetent (2005, as cited in Saxton, 2007, p13). In this case, does the reality attached to the physical media no longer pose a stimulation or a threat to the audience, but gradually become an item that can be examined, so we become numb and rigid filled with such empty realistic derivatives to some extent? The surprise when people first time see the images has gone. According to Yuan (2017),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flood of information and also the large proliferation, modern media can cause the implosion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virtual. Being the product of human being, modern media like television and content included inside gradually convey and then even represent the spiritual world of one. In the life surrounded by multiple media,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is almost inevitable.
In Caché (Haneke, 2005), the video tape is one materialized physical convey of Georges’ emotional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guilty he cannot forget when he deliberately uses lies to get rid of Majid in his childhood. The video tapes lead Georges in to the infinite maze of memory and escape.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identity of Georges is the host of a television show, the producer of the medium society. Frame start with the scene in video tape, which is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present reality at first, and then frame jumps to another scene that turns to be seen as happening in progress. Each video tape sent has occupied the full screen for a while, which is equal with the ongoing film scene. Counting the film as a medium itself, there almost is no a certain space for audience to be present except the truth, being in front a screen, that may already had been forgotten. Georges keeps trying to find where the camera is by walking around the same place recorded in video tape.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find the camera since the source of tapes are actually from director’s sight or audience’s sight. Alienation happened before all the people realized it, the “video tapes” had controlled us.Word count: 514Reference List: Heiduschka, V. (Producer), & Haneke, M. (Screenwriter/ Director). (2005). Caché [Motion Picture]. French: Wega Film etc. Saxton, L. (2007) Secrets and relationships: Off-screen space in Michael Haneke’s Caché.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Yuan, X. (2017). Michael Haneke’s film studies: The sin that be shadowed and highlighted. Wuhan: University of Wuhan.
3 ) 一个笑话和一道触目惊心的血光
一部讲述真相的电影,隐晦地提及了上世纪60年代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关联的伤口,多年后的梦魇中乔治遇见了童年时的恐慌,只是他依然在狡辩中寻找着借口。
首尾两个长镜头交代了故事由来并且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透露着某些希望。
揭示故事悲剧来源是影片倒数第二个场景里的长镜头,清冷的图像中,6岁时候的乔治在低暗角落里目睹了马瑞特在挣扎哭喊中被收养院的车子带走,他达到了期望的目的。
Cache的特别之处在于设置了一个不曾存在的摄像机,伴随着全片的丝许沉闷在最后带来的更多是自省,不多的亮点来自一个笑话和一道触目惊心的血光。
1995年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的马修.卡索维茨用黑白影像讲述了巴黎郊区的社会暴力,巧合的是2005年《Cache》上映后几周巴黎市郊发生一系列骚乱,肇事者正是非洲移民的后裔。
我说摄像机不曾存在是基于乔治揣测寄送录象带人的动机根本不成立,敲诈?
恶作剧?
都不是,这一切不过是把乔治指引向了童年的谎言,那些他漠视或者不以为然的伤害,又以马瑞特的自刎划终。
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不应该是现实中某人所为,或者用神乃至上帝的视角来解释。
正是乔治身上中产阶级的虚伪或者说小时候的自私,姑且我们说他是自私,毕竟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倒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心计。
不过这依然非常致命,中年时候的马瑞特穷困潦倒,又被平白无故地横加指责、威胁恐吓乃至拘留,而这一切竟是来源于小时侯的朋友。
实际上正是乔治所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才有了多年后的梦魇,问心无愧也并说嘴边说说那么简单。
马瑞特小时侯被欺骗,中年时候又被冤枉,一次被驱逐,一次选择了自杀,看似并无联系,实际上都是作为外来族群所遭受的排斥,如此说来哈内克的野心又实在来得有点大。
其实想说的更多,或许看这个片子确实需要一定的耐心。
4 ) 《偷拍──隐藏的恐惧与罪疚》
《偷拍》(Hidden,又译《隐藏的恐惧》)的导演米高.汉尼卡(Michael Haneke)接受访问时指出:「同一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观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层次:个人层次、家庭层次、社会层次、政治层次。
电影提出的道德问题是,如何处理罪疚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时候,宁愿隐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隐藏的角落,我们都感觉到罪疚……」[1]对于《偷拍》的男主角佐治(Georges)个人来说,他的隐藏角落是马哲特(Majid),一个阿尔及利亚孤儿,他的父母因1961年屠杀事件而下落不明。
佐治在童年时因私心而诬告马哲特恐吓自己,令父母打消收养的念头,将马哲特送到孤儿院去。
这个童年的阴影成为佐治的罪疚重负。
汉尼卡所言非虚,同一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观看,除了站在佐治的个人层次出发,也可以循着社会政治层次出发,将佐治与马哲特的关系提升到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政治层面。
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从1954年开始发生了旷持八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可参考电影《阿尔及尔之战》(Gillo Pontecorvo,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
其中1961年10月17日,三万名阿尔及利亚人应民族解放阵线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FLN)的号召到巴黎示威抗议,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事件后来酿成了血腥屠杀,许多示威者被法国警方殴打至昏迷,甚至有示威者被丢到塞纳-马恩省河中去,遇溺身亡,死者数目至今不明。
事件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禁区,直至1999年才被官方证实[2]。
法国政府不敢正视面对,多年来没有为往昔的罪疚而忏悔。
早在1945年,反战的加缪已经说过:「今日之世界,各方面都充斥着仇恨,到处都有暴力和武力,到处都有屠杀和喧嚣,它们把空气搞得污浊不堪,使我们如置身于可怕的毒雾之中。
我们所能做的,无论是为谋求法兰西的真理还是人类的真理,我们都应该使之为反对仇恨而努力。
」事隔十年,加缪在一封信中说:「我愿意相信,并且极力相信,和平,将在我们的田野上显现,将在我们的丛山和海岸上显现。
那时候,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会在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重新和解,那时我们将努力忘却把我们两个民族分隔开来的今日之鲜血。
」[3]然而,今日之世界仍充满仇恨和绝望,人类仍未回归和平的故乡。
《偷拍》中出现的中东冲突新闻片段,正是西方世界的隐藏角落,也是西方世界的罪疚重负。
从每个人到每个国家,都必然有罪与不义,电影中的佐治将不名誉的过去深深隐藏,直至那些神秘录像与图画送到家门,他才尝试面对过去的自私和罪,然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悔意,当他吞下安眠药,睡一觉,一切彷佛不曾发生。
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日本与中国、美国与中东都充满仇恨,后者等待前者的忏悔,但前者等待后者的宽恕吗?
马哲特与佐治的儿子真的在片末一幕谈话了吗?
我看不见,但我宁愿相信自己看见了他们的和解。
关于罪和恐惧,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在《恐惧的概念》一书中早已谈论:「罪进入恐惧,但罪反过来又带来了恐惧。
当然,现实的罪是没有持久性的。
一方面,罪的持续性带来恐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拯救的可能性又是一种虚无,个体既爱又怕,因为个体与此恒常有可能性的关系。
只有拯救实际上确定的一刻,恐惧才被克服。
」[4]罪和恐惧是共生的概念,在拯救之先,罪和恐惧是不能被克服的现实状态,而恐惧是因罪而带来的一种可能性。
齐克果又指出:「如果我因过去的罪过而恐惧,这是因为我没有将它与我的实质关系放在过去的欺诈行径上,或者另一人阻止它成为过去。
若果真的过去,那么我不会恐惧,而只有忏悔。
」[5]只有忏悔,罪被确立,恐惧才会消失。
在《隐藏的恐惧》中,佐治对于过去的私心一直没有忏悔,他可能将那一件童年往事抛诸脑后,但罪的持续性并没有消失,阿尔及利亚人马哲特两代都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学懂的是仇恨。
神秘录像与图画带来了恐惧的可能性,但佐治并没有投入信心之浮木,寻求拯救之船,衷心忏悔,一如齐克果所指的,人必需要真诚面对可能性,并持有信仰,恐惧才有教益,人也在赎罪中安息。
电影中的佐治是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正好表明了他的恐惧与不安。
最后,马哲特与佐治的儿子到底是和解还是引起了另一重的仇恨呢?
观众并不知道。
到底,那些神秘录像与图画是谁做的呢?
观众也不知道。
因为佐治是被观看者,观众是观看者,也是被观看者,唯有超然的审判者是观看者,终极的观看者,看着佐治,看着我,也看着你。
[1] http://www.brightlightsfilm.com/50/hanekeiv.htm[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is_massacre_of_1961[3] 加缪(2002),《加缪全集》,石家庄市:河北敎育出版社,页292、296[4] Soren Kierkegaard(1980),The concept of anxiety : a simple psychologically orienting deliberation on the dogmatic issue of hereditary sin,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53[5] 同上,p.91-92(刊登于《月台》第六期)
5 ) 上帝已死,我心为王
Caché有些令人不快地摆出一副用下巴颏瞧人的模样,披着侦探悬疑+心灵扭曲+家庭伦理的外衣,讲述了一个半陈半新的主题:“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人人都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而且他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种种罪行进行惩罚和清算。
作为主线交待的Georges多数是个偏执狂+妄想症患者,他固执地认准了一个要对他的生活进行破坏性报复的敌人,一厢情愿地发着被迫害的梦。
他的罪是不知内疚,妄与执,缺乏畏惧,不知自醒。
录像带便是提醒他不要忘记曾经对别人的伤害,线索指引他穿越记忆和眼下殷实富足的生活,逼他直接与当年的受害者四目相对。
你忘记的罪过,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总不会悄无声息地就这样如雾气般散去,而是一定会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而且一定会受到审判,不一定是法庭开庭,宣判被告入狱,而是像电影里一样,你呼吸的空气里不再轻松,而是充满了压迫和紧张,正是那“我不杀伊人,伊人却因我而死”。
有了罪过终究会有报应,倒是颇有我们文化传统里“善恶终有报”的意味。
Anna与朋友Pierre见面的亲密场面被她儿子目睹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背负自己的行为的后果。
说Caché叫人不爽是导演颇有些越俎代庖的感觉,将摄影机代替上帝之眼,片中一个电视台主管对Georges说过一句话“这是个多神的国家”。
Caché不像《七宗罪》一样充满浓厚的宗教意味,没有圣经的线索,也不使用类似Air On the G String这样如祈祷般肃穆而宁静的配乐,在Caché的世界里,导演的摄影机成了全息的神。
不仅仅是美国,法国也有大量的外国移民加上本土法国人加上以前殖民地的人们,文化的冲撞同样巨大,前阵子的巴黎骚乱似乎也是因此而起,宣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也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和贫富差距(偶尔关心一下国际政治的我小心翼翼地发言)。
片中Georges在6岁颇有心计的伤害的孩子正是阿尔及利亚裔的,这种符号化的象征在片中出现显然不是一种偶然,法国农庄主的孩子因为害怕自己的生活被家中帮工的孩子分享而陷害了他,被人误解是有危险性的疯子,得不到原先可能的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最终导致的是这个孩子在中年之时为了表明没有恐吓窥视Georges的生活,而极端地选择自杀。
或许可以解读成一个对自己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而惶恐的人/党派/国家/利益集团对另一个相对弱势的人/党派/国家/利益集团的心思缜密的伤害。
Caché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让Michael Haneke继2001年《钢琴教师》之后再度拿到了最佳导演奖,也许不是因为Michael Haneke装上帝,而是因为这个电影承载着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人性、伦理、道德、政治……诸如此类。
6 ) cache
--yolfilm說真的,我真討厭這電影。
這是個大家都要「改良電影語言」、「發明電影語言」的時代。
是呀,這是所有電影人都夢想的不世偉業,從剪接的波特、愛森斯坦、普多夫金,到不剪接的薩耶吉地雷,到低角度的小津,到肩拍的高達,到卯起來用zoom鏡頭的六零年代諸公們,比如法斯賓達,甚至連變形鏡頭,超寬銀幕,連大衛連,到用穩定器攝影器材、還有超高感光底片的庫柏力克,能算上的,全算上吧。
這條浩盪的大路,前撲後繼多少人來?大家都想在作影史上,「另起一章」的偉大人物。
從某某某人開始,電影語言,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cache,當然也是其中一部,我猜,當然,只是我的猜想呀,我猜,他又想「改良電影語言」了。
嗯嗯,我這是全新的文本,全新的敘事手法,全新的電影觀影角度,我就該以我為名。
從今天開始,馬克_思主_義,到了我這裏,改叫列_寧主_義,然後,等著後面又來一個史達_林主_義,緊接著,xxx思想,xxx理論,一個一個排著隊,全都等著進史書裏去。
當然,cache這電影,最多,我也只能說是電影語言的「改良」,因為,沒有到達「發明電影語言」的位階。
我相信導演自己也不敢居高吧,要說「發明」,就得是一套全新的架構,有東西在後面支撐,也許是寫本大部頭理論書什麼的,也許是徒子徒孫一堆,帶出來一個新世代什麼的,要說「發明」電影語言,總要有那個高度在。
我相信,這個導演也該知道自已的斤兩吧?
因為,我看到的cache,確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玩意。
雖然他很想。
確實想,想的發狂了,把電影很死裏整,但,我覺得,這cache,且不說發明二字,連改良都很難上算 。
這片子是那樣的「屈從」,表面上,他不在乎給你完整的敘事,他裝作不在乎,但事實上,他又忍不住要在片子裏提醒你。
這就是屈從。
說不清故事,並不是電影語言的進步,而是一種退化。
達爾文早告訴我們,物種是會退化的,不一定會無止境地進步下去,有時,也會退化到之前的低階狀態。
我真不懂,為什麼有人會認為cache是一種電影文本的新發展,這玩意根本不是的,它太操蛋了。
就說一點好了。
男主角的孩子離家出走了一晚上,ok,第二天回來了,演媽媽的畢諾許,問他兒子,咋回事,你要說喲,不說,我怎麼知道。
孩子說道,去問皮埃爾吧,他比我清楚。
這皮埃爾是誰呢?
就是前頭,畢諾許跟老公發無名火,在小咖啡廳裏,趴在對方肩膀哭的那個男人,是的,這個皮埃爾一直在主角家中出現,但,真正的,和畢諾許有親暱舉動,全片也就是這場戲。
而這場戲,沒有別人在場。
(可我們觀眾看到了,不是?
)這就是最低階的好萊塢標準語法,用全知的第三人稱,提醒你,片中還有第二人稱的存在。
觀眾看到了,片子裏,孩子也說出口了,ok,我們可以推論,定是那個現場,畢諾許和皮埃爾有親暱舉動的現場,還有其它人在。
這個目睹現場的人是誰呢?
這個跟觀眾一樣地見到了畢諾許和皮埃爾親密靠在一起的人,是誰呢?
是誰不管,但,這個誰,也許是阿爾及利亞男人,也許是他兒子,也許是畢諾許自已的兒子,總是,這幾個人之中有情報流通的管道。
不知道看懂我的意思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導演表面上要你看不懂,要你去猜,但,他還是守著擔憂害怕,偷偷守著分寸,表面上讓你看不明白,其實,他是巴不得你搞清楚。
就像主角的兒子離家出走,是誤會母親紅杏出牆,這紅杏出牆,總要讓觀眾看到了,這看到了,加上兒子的行為,鏡頭外,人物關係的祕密聯繫,就被建立了。
也因些,我們能確信,主角的兒子有參與到這件事裏面來,跟片尾最後一個鏡頭是呼應的。
千萬別忘了片尾的鏡頭,大家不是都在銀幕裏找人嗎?
都說,喲,本片最後一個鏡頭,主角兒子,和阿爾吉利亞男人的兒子,有在一起說話喲。
這,就是屈從。
所謂的屈從,還表現在一些小地方。
比如片子裏的說謊,吃飯的晚上,有人說了一個非常無聊的笑話,說半天,整一個是謊話來的,這個謊話的題旨,在哪裏被加強了?
在主角主持節目,進剪接室,也是把來賓的不良發言砍去。
這個謊話的題旨,在哪裏被裏被加強了?
在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間,在男主角和母親之間,在男主角和老板之間,在許許多多的地方,用一些很低階的手法,多一半全是靠著台辭的表現,而被加強了。
說到底,這導演,不是故意不說故事,他只是歪著說,又說不好,佈的局不明確,但又無能為力,但,又怕你看不懂,這邊放一點,那邊放一點,留下一堆線索讓你去有「發掘」的快感。
他擺明了,就是要讓你去聯想,去解謎。
就像最後一個鏡頭,他就是要你去寫上幾千幾百字的文章,你寫了,你發掘了,你提問了,他就贏了。
怎麼會有這樣操蛋的電影呢?
這樣操蛋的東西,打從九零年代該死的逗馬九五開始,基本上就是當今影壇的主流了。
舉凡影展,都要這樣抬高無意義的嚐試,帶著頭吹捧這樣的作品。
死了逗馬,又來新的「雞雞文本電影」理論。
理論兩個字,哪是這樣簡單就能被創造出來的?
理論,是有大量的智性在活動。
cache裏的智性在哪裏呢?
請千萬不要告訴我,在那個「不知道誰拍了錄影帶」喲。
因為,人家導演拼命想要暗示你,確實是阿爾吉利亞人的兒子拍的喲。
阿爾吉利亞人為什麼要自殺?
為什麼那天晚上被帶去警局時,在車上要流淚不止?
他當然是有理由的,他把自已可憐的一生歸罪在男主角身上,而且,他作的最大錯誤是,他告訴了自己的兒子,把仇恨種植在兒子身上。
兒子作的這些事,他都知道,所以他會哭,警車上哭,家裏也哭。
他看到男主角拿的那張圖,一看,就瞭了,噗通一下,軟了,沒力地坐在椅子上。
這些,都是細節,為了怕觀眾不明白,後面又來一大段戲,讓阿爾吉利亞人死了之後,他兒子又去大鬧男主角的公司,說了一堆屁話。
當然,其中有說謊的成份(別忘了,本片中,一直在強調「說謊」二字,雖然有氣無力……)。
因為片子裏,到處有人在說謊,所以,阿爾吉利亞人的兒子說,片子不是他拍的,八成是謊話。
最後一場戲,根本不是交代兩家人的兒子有相通,不是的,而是在佈一個驚悚的局,跟你說,男主角,你睡吧,你別想安心喲,我們阿爾吉利亞人的兒子,復仇計劃未停,他正在打你兒子的主意……。
說了一堆,說得我舌頭都打結了。
其實,這也就是一部,原來想拍出驚悚類型的電影,想跟「性、謊言、錄影帶」追美的玩意,但,導演的手法技巧實在是欠奉,故作玄虛,拍成今日之模樣。
也因此,會有一群追捧莫唬爛大道,一群追捧逗馬九五的歐陸專家們,追捧這玩意,變成了年度的傑作。
真是夠了呀。
傑作個球。
7 ) 还魂的影像:二次加害者的自指与自反
原文发表于“半斤八两抡电影”公众号,作者半斤。
1961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巴黎警方宣布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实施宵禁,此举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民族解放阵线号召阿尔及利亚人集会抗议。
人们走上巴黎街头,巴黎警察总长帕蓬 (Maurice Papon)下令镇压,暴力殴打很快演变为屠杀,有超过二百具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被扔到塞纳河上。
这段历史,直到20世纪末才被法国正式承认。
2005年,迈克尔·哈内克在《隐藏摄影机》中,借助近乎悬疑片的结构,让主人公追索自己幼年时期的罪行,进而引出了这桩被历史掩埋的暴行。
主人公乔治,是当红的电视台主播,主持一档读书谈话节目。
他的妻子安娜,供职于一家出版公司,她的老板也是她们夫妻的好友。
两人育有一子,皮埃罗,正在读初中。
一家三口过着精致的中产生活,和美平稳。
一天,夫妻俩收到一盘匿名寄来的录像带,放出影像后发现自己的生活日常被人偷拍。
随后,安娜接到匿名电话,乔治在电视台收到明信片,匿名者以简笔画手法画了一张正在吐血的脸,神情惊恐。
随着皮埃罗也收到了类似的明信片,乔治夫妇又陆续收到了内容不同的录像带,随带附寄的还有风格统一的简笔画:吐血的人、被杀的鸡,脖颈的血喷溅而出。
随后的录像带记录的影像,让乔治越来越确信这与自己幼年的经历有关,恐慌日益加剧,他决定找到“恐吓者”,维护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故事讲到这儿,悬疑类型的味道已经做足,如果不是哈内克,故事的调子势必一番狗血:一个中年有成的白人男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战胜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只是,哈内克的笔锋陡然一转,把审视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位白人中产男性身上。
正是这一段又一段的窥视影像,逼着乔治重新面对自己的黑暗过去。
故事讲到这里,如果不是哈内克,往下发展无外乎就是个类型变体的套路——乔治忏悔自己的罪,与“威胁”握手言和,回归既定轨道。
可是,哈内克用这个幽灵般的“偷拍者”,激发了乔治的恶,让他再次加害了他曾经伤害过的对象。
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两次加害的全貌,两个时空并置,消解了悬疑类型的套路,被窥视的不安感通过电影带给所有人,每一个观看者,在这审判般的窥视里,无所遁形。
乔治——中产阶级的代表——拥有媒体话语权的名人,他所担忧的“威胁”究竟是否构成真正的威胁?
他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合法”权益(包括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他拥有的财富、家庭、名声)——进行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对受害者的再次加害。
《隐藏摄影机》里出现过的影像,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承担寻常叙事功能的影像,以所谓的“全知视角”呈现,交代故事中所有角色的行动;二是窥视影像,以录像带为媒介,属于未知视点,是在被记录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摄到的影像;三是乔治担任主持人的谈话节目,呈现在电视荧屏和电视台剪辑室的显示屏上;四是乔治家电视播放的新闻影像,涉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遭受“非典”疫情的中国的街头采访等。
其中,第二类窥视影像可以被倒带并反复观看,影像本身既是谜题也含藏着解谜索引,引出“悬念”,作为叙事动力的一部分。
第三类是乔治团队完全掌控的节目影像,可依循乔治的个人意志被剪辑,甚至抹除。
第二类和第三类影像,在“真实”这个意义层面,是完全对立的存在。
而在第四类——新闻影像的对比之下,第三类影像更显得精致而虚伪,是包裹着糖衣的意识形态巨网。
这四类影像共同作用在乔治身上,刚好形成悖反的关于“真实”的指涉。
乔治可以随意掌控第三类影像,但是对第二类影像束手无策,他受困在偷拍的影像中,面对着他一直试图遗忘甚至要抹除的罪行,他的社会地位因之动摇,他的冷酷和虚伪因之暴露。
第三类影像——读书谈话节目,这类影像从被记录之前就被言说者们刻意矫饰编排,他(她)们坐在演播室侃侃而谈,修补着作为文化中产者们的面具,最终经过乔治的再次矫饰,呈现在荧屏上,操控着观众们。
观众包括了乔治的家人,朋友,也包括更低阶级的观众,如被加害者马基德。
马基德曾经看过乔治主持的节目,他也与乔治的长辈亲人、朋友家人一样,是只能被动观看的观众。
就像《班尼的录像带》,无名女孩被班尼带回家,她只有看的份儿,根本不能动摇班尼的影像话语权。
但是,在《隐藏摄影机》中,哈内克让被害人反抗了——无论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
以生命献祭的马基德成功了,他成了窥视影像的主体。
马基德的割喉“反抗”,借由第二类影像——无论是不是他拍摄的或寄送的——他都在这真实影像里,彻底洞穿了加害者——乔治的面具和铠甲。
第二类影像之所以锐利,正在于它记录了“生活”本身。
在第二类影像里,未经剪辑的窥视影像,其拍摄时间就是真实的时间,而空间则经由镜头里所有的参照物被证实为真。
在完全真实的时空里,影像记录的对象——因其不知道自己被偷拍——所发出的言行,剥离了全部的虚矫。
乔治气急败坏的威胁、马基德伤心欲绝的独自痛哭、马基德决绝的割喉、乔治冷漠的见证,甚至片尾放学时所有学生的放松的言行,包括马基德之子和乔治之子平等融洽的交谈……这一切都是哈内克在影片中建构并强调的“真实”。
《隐藏摄影机》里,无论偷拍者是谁,其窥视影像都忠实记录了马基德被乔治恶语相向甚至恐吓威胁的全过程,这使得马基德被加害的事实被记录,并被众人所知。
更要紧的是,偷拍者记录了乔治走后,马基德独自痛哭一小时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被乔治的妻子看到,至少被乔治的老板(老板秘书)看到,至少被马基德的儿子看到。
乔治对马基德的伤害,在各个阶层面前都被暴露了至少一次。
哈内克的悲悯,正在于他记录了被加害者的痛苦,他拒绝遗忘,拒绝把视线转开,他忠实记录了加害者的二次伤害。
马基德的父母被1960年代的暴力机器杀害,幼年的马基德本有可能被乔治父母收养而获得崭新的人生,却被乔治设计陷害,终遭驱逐。
中年马基德被乔治指控绑架了皮埃罗,被警察粗暴入户抓走,失去了仅剩的尊严。
哈内克直接呈现出加害的过程,正是他对被加害者的关照。
未知的窥视影像,其实并不能威胁乔治一家,它之所以被认定是“威胁”,只是因它的“真实”,因为它一直盯着乔治,这份凝视唤醒了乔治掩盖已久的人性黑洞。
他在怀疑和调查的过程中始终对妻子隐瞒实情,堂皇的理由正是为了“保护妻儿”。
而安娜也并非坦诚如一,儿子的“失踪”刚好揭开了安娜和老板之间的暧昧关系。
如果说窥视影像对节目影像发起的是毁灭性的穿刺,那么新闻影像则对叙事影像做出了若有若无的解构。
生活的琐碎本真,击碎了虚矫和操控;而现场直击的新闻记录,则不停介入甚至干扰着乔治夫妇的对话——那是在精心雕琢的消费之下的中产居家生活,是被物化的精致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乔治夫妇之间,展开的对话是暗流涌动的角力。
正因为不断插入的新闻影像,他俩的对话张力得以绷到极限。
伴随着乔治和安娜的对话,新闻影像里的内容,处在“非典”疫情恐慌之下的街头和戴着口罩的急救车司机、笼罩在联军角力的氛围之下被战争摧残的伊拉克民众……影像中的寻常人遭受着致命传染病与战争,而他们的苦难只作为乔治和安娜的对话背景存在,这对中产夫妻漫不经心地切换频道,同时试图推理出偷拍他们的“恶作剧”坏人,他们所担忧的轻与新闻影像里人们所遭受的重,成为反讽的对照,是另一组悖反式的生活断面集合。
在哈内克严谨的对仗建构下,影片以窥视影像开始,从家门口生活的真实断面开始,借由遥控器和观众(乔治和安娜),转化成为中产居所的电视荧屏里的“幽灵”,打破了稳定有序的生活。
偷拍的影像和不祥的明信片乌云般积聚起来,当窥视影像遮蔽了乔治的天空——他的起居空间、他的工作空间、他的过去的成长空间……悬念逐渐超越了悬念本身,成为吊在乔治头上的镰刀。
他由此惶惶不可终日,他掩盖的过去和矫饰的当下——都被揭开。
《隐藏摄影机》在记录加害过程的同时,始终凝视着拍摄对象,直指中产阶级永远丢不掉的阶级恐惧。
对乔治们而言,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现有的社会地位。
乔治的父母是农庄主,而马基德的父母是长工,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因为确定而彼此相安,在马基德的父母死后,乔治的父母可以大发慈悲收养马基德。
而幼年的乔治陷害马基德的伎俩,刚好戳中了乔治父母的要害——他们担心马基德带有传染病,这将成为农场主家庭的最致命威胁。
因此,乔治的父母半推半就地放逐了马基德,正如历史上欧洲中产对犹太人所做的,他们任由马基德被带走、甘愿被乔治欺骗,完成了中产家庭的“平庸之恶”。
与父母不同,乔治选择了权力新贵——媒体,作为他大展拳脚的舞台,收割财富与名声。
马基德久别重逢还憨憨地问乔治“你没有继承农庄?
”——这份短视令人心碎。
而乔治,作为新的话语权的代言人,他面对的威胁被哈内克设计为媒体内部的威胁——窥视的真实影像威胁着造作的虚假节目。
颇富意味的是,窥视影像最终指向了一处明显是被作者特意挑选的街道名称——“列宁大道”,这个名字,代表了某种力量,正是乔治们所担心的力量。
在哈内克严谨的对仗建构下,影片以窥视影像结束。
皮埃罗放学后,他的校友和同窗几乎都成了被窥视的对象,他们无忧无虑地彼此告别、闲扯,对“隐藏”摄影机毫无察觉。
除了马基德之子(他不属于放学影像的被拍摄主体,他是由画面右下角入画,到画面左上角招呼皮埃罗,再到画面左下角与皮埃罗寒暄,最后再从画面右下角出画),他对于皮埃罗就读的学校的学生们而言,始终是另一阶级的“他者”。
在窥视影像的“真实”里,第三代被加害者也只是个“过客”,他的入画和出画将与这段窥视影像形成“共谋”,将一并成为藏在幽暗处的威胁着第三代中产们的“幽灵”。
与第一代的雇佣关系、第二代的敌对关系不同,第三代之间的相处更为轻松,表面上更为平等宽容。
但是,是否真如哈内克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的,他给出了下一代之间的更为包容的未来可能呢?
不,只要他们都处于窥视影像里,他们之间的裂隙将永远存在。
乔治代表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低下阶层有天然的逼退力量。
他们越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和阶级地位,就越会逼退低下阶层的零星希望,最终,劳动者阶层只有喷溅自己的血,才能在中产的记忆里留下痕迹。
焦虑——失去阶级地位的焦虑,成为中产阶级们的软肋,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们无限侵占、逼退、加害低下阶层者们的动因。
其实,相较于脆弱的马基德,窥视影像才是真正的“幽灵”。
威胁着乔治们的,根本不是马基德们,而是他们自己发现并利用的影像媒介。
正因为窥视影像的出现,马基德才会被乔治步步逼近,最终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反击。
可以说,窥视影像作为影像媒介的一部分,既让乔治感到威胁,也导致了马基德的自杀。
隐藏摄影机的存在,对加害人和被害者都构成潜在威胁,体现出无差别的残酷,等同于“真实”带来的沉重和锋利。
《隐藏摄影机》带来的彻骨冷意,在于乔治压根儿没有愧疚,在受害者面前,他甚至懒得掩饰。
在电视台老板——能决定乔治命运的人面前,乔治自己则伪装成了“受害者”。
作为媒体宠儿,为了自保,乔治能轻车熟路地阐释偷拍影像,甚至扭曲“真实”。
这也是继《班尼的录像带》之后,乔治代表中产阶级体现出的新时代“大能”。
掩盖罪行的本能,会成为第二次加害的恶之种子。
如何避免无限的加害循环?
哈内克给出了他的方式——显影并记录罪行!
《班尼的录像带》结尾,班尼用自己拍摄的纪实影像揭发了父母的罪行。
而《隐藏摄影机》,则是通过窥视影像叩问了乔治对马基德的第一次加害,同时又记录了乔治对马基德的第二次加害。
这是一次对被加害者的还魂,正如乔治睡着后出现的幼年段落,小马基德挣扎着被孤儿院的老师拖进汽车带走,这一段落的视点,则是1960年代的“隐藏摄影机”的视点。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说回到1961年的巴黎“屠夫”警察局总长——帕蓬。
帕蓬曾在维希政权时期任职波尔多,在1942年到1944年间,他逮捕并遣送超过一千五百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后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帕蓬,这个纳粹主义的施暴者,在二十年间,两次站在了加害者的位置。
塞纳河上被虐打至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冤魂,经由哈内克精密的影像自反,再次浮出历史的冥河。
偷拍的影像,叩问着当代人主动泯灭的良知。
图文编辑:克莱尔的燃烧弹
8 ) 平静的影像,颤抖的心绪
当乔治与妻子开始收到偷拍他们家门前的长镜头录像带与画有小孩吐血的漫画后,平稳的家庭开始出现了异样不安的现状,这些浮躁不安感真正的根源来自于当代生活中人们对周遭生存处境内心隐存的焦虑与猜忌。
而人们最焦虑与恐慌的其中就是害怕内心“真相”的揭露,每个人深藏内心的自我“真相”、“秘密”。
当自我的秘密或真相被外在任何具威胁元素侵袭介入(揭露)时,个人、群体努力建构、“包装”的生活就会被层层剖解、挖掘、引发出人性真实原始,甚至丑陋的一面。
人们为了消除这些自认会对自我产生威胁的人、事件或事物,也许就会以自认正当必然的行动但实为变相的罪行去反击“侵略者”,使得人性的罪恶永无止尽且不断的伪装与蔓延下去。
片中的隐藏摄影机也许只是导演借用的一个符号手段、一个引子,藉此传达出影片欲指向、通往人性的种种审视与尝试挖掘、直面生存潜藏不安的根源,也许是罪恶的、暴力的、无理的、荒谬的、逼迫的。
影像是异常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但面对这样的主题着实让观者内心无法平静,因为躲藏(CACHE)的摄影机就是我们内心的那股黑暗角落!
9 ) 中产阶级赤裸着
电影的现实时间画面与监视画面保持统一的现实主义影调,不同于其他电影总会给监视画面加上装饰性暗示——压缩画质导致的横条、角落里REC或时间的提示。
不会有观众看到便知第一画的静止长镜头就是夫妇在观看的监视画面,是她们的声音入场以及后面的剧情交代我们才推论出这个次序。
而片名与主创也出现在这一画面里,它就像是作者拍的、他需要给出信息或传递美感的镜头,并选择它刻上自己的烙印。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在类型片里它需要做到完全欺骗,要让观众相信这的的确确是监视画面,是监视人的第三者行为;然而在这部电影里作者这么拍摄、处理、拼接的目的不在于突出现实性,而在于表明监视人即作者这一事实。
如果监视画面和现实时间画面同出自作者视角,那显然它打破了电影的内部结构,或者说,作者作为超验的存在——上帝之眼审视着这一切。
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从某个场景中无缘由地、突然中断地切到下一场景也就像录影带突然的ending,可以说是哈内克给(看电影的)妳寄了一盘录影带;而且他从铺垫事件的前半段就已经不避讳地使用这种手法,既是信任我们的信息组织能力,又是在说明:「我」(作者)在有选择且阶段性地释放信息,而观众和影片中的夫妇一样,只能根据已接收的信息给出判断。
显然这蛮自恋的。
最明显的是第二回夫妇收到的录影带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现实时间画面,因为没有画外音;但第二次出现时,是男主到家后回放的监视画面,反倒在此时出现了咳血男孩的反打画面。
佐证了如前所说的,作者不在乎是否突出了现实性,甚至可以在这种时刻像黑洞折叠一样将不同的时空影像剪接在一起。
(顺便一提,梦境的画面反倒比现实时间画面更清晰而没有杂质,现实时间画面和监视画面都带有明显的边缘颗粒感,是一种仿录像带的影像)此时咳血男孩的画面是男主的臆想,因为从后一秒夫妇的对话中我们得知男主在看录影带时走神了,而当时她们是第一次收到咳血男孩的画,他从第一次看见画就知道是谁,可窥见其内心深埋的恐惧之冰山一角。
此处的打光和构图十分古典主义,像一个忏悔室那是怎样的强大动力使得他一直试图掩盖童年往事?
也是同样的恐惧。
记得反派影评有一期节目里,嘉宾靳锦说过:「孩童有天然的阶级意识且对此毫无反思。
」(大意)那么在缺乏教化的时代里,亲历成年人的党同伐异——1961年巴黎惨案,一个法国白人地主儿子对收养的阿尔及利亚黑人长工儿子的污名化迫害就不止是简单的阋墙谇帚,而是一场由阶级、国族、历史掀起的巨浪,荡至某个乡村农场里的浪花。
它却足以改变一个儿童的未来走向,余波直至今日,杀死了他。
当然,马吉的自杀也是因为看清了将他推入深渊(孤儿院)的乔治没有一丝悔意,然而观众知道乔治挥之不去的梦魇(梦魇里马吉怒杀公鸡似乎也是对阿尔及利亚报复高卢雄鸡的恐惧),他漠然的姿态越决绝,我们越能感受到他的恐惧。
乔治的恐惧和冷漠即是法国政府1961年巴黎惨案长达37年的否认和舆论管控;他在几十年后见到当年被自己迫害的马吉却丝毫不过问他的生活,就是中产阶级(或如他口所说的「社会精英」)对底层的不过问、不在意。
它们出自同样的恐惧,恐惧阶级掉落,恐惧政治清算,恐惧家庭事业等一切关乎自身利益的损害,恐惧一切经自己之手坠入深渊的亡魂的哭泣、咳血……大可以不信这些,继续高谈阔论的电视节目,出入灯红酒绿的party,享受书迷与同事们的笑面迎迎,甚至回头嘲讽、消解这些沉重的包袱——在朋友聚会上一位配角花几分钟时间只是讲出一关于转世的笑话,而最后只有一名黑人女性还在疑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似乎也带有一种历史指向。
当然,她们可以嘲笑转世,也就更可以不信因果报应。
然而当乔治被上级招至办公室时,面对自身利益受威胁时,却可以安心说出「愿上帝有耳」,如果隐藏的摄像机即上帝之眼,那么即使上帝把录影带都寄到他家,他也不为所动。
因为身边尽是需维护的自身利益,维护家庭、房子、事业等代表中产的一切似乎令做噩梦成为了微乎其微的代价。
但她们的家庭内部又是如此不堪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言语的冒犯与信任的缺失令情感无处疏通,而且,或相敬如宾或针锋相对的关系已经使情感僵化,在外部力量面前多么脆弱。
与核心事件无关的儿子出走,既点出了孩童的敏感,又如手术刀般再一次剌开这个中产家庭的伤口。
但也并不能划分清楚个人过错,因为她们彼此互不沟通,所以夫妇不知道皮耶侯的想法,安娜不知道乔治的猜疑与梦魇,乔治不知道安娜的情绪无处抒发,也不知道安娜和皮耶的关系……安娜作为代替观众追问乔治和马吉的过去的角色,没有因此被作者多设计任何让人同情的特征,除了遇到重压时更外露的难过,但本质上她和乔治是同类人。
她也可以给一个丈夫童年时伤害的人的哭泣片段揿暂停键,她不会在丈夫将马吉在面前自杀的事实与过去犯下的错和盘托出时展露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仅仅只是抚下他的肩膀;正因为中产阶级在哈内克的镜头下是虚伪的、懦弱的、自私的、带有原罪的、互不信任的,它的影像如数学推导、论文举证般立场先行地进行人物塑造,概念先行地引出故事情节。
在1961年10月17日血腥镇压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国政府亦是如此,是多么强大的阶级/政治共同体的自保能量,让它或是乔治,可以没有丝毫愧疚地面对死在面前的受难者,然后在之后的无数年也闭之不谈。
然而乔治还是会在很多年后,赤裸全身进入梦乡时,梦见曾真实发生的农场画面——马吉被推入深渊的过程,就像几百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沉尸塞纳河。
而当下,电视机播放的殖民地新闻仍旧发生着……
电视机里播放着殖民地新闻这不需要我们做到文化语境层面的设身处地,我们最有资格感同身受,因为曾经如此,现在没有自省,将来还必回到原地。
结局镜头停在儿子皮耶侯的学校门口,却不见皮耶侯,或许在暗示他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了,但学校之意味还在叩问着,我们要留给下一代怎样的历史?
10 ) 隐与显
20250320-大光明哈内克回顾展。
《隐藏的摄像机》英国《卫报》称这是21世纪第一部伟大作品。
1961年巴黎塞纳河屠杀事件虽然在电影里只是一句台词带过,“隐的不能再隐”,但却是此片最重要事实基石。
“谁拍的录像”,是片中最彰显线索,到最后反而一点儿都不重要了,因为事实就在那儿!
(据说此片是头一次把这个被法国政府可以低调处理的事件,放到大众面前,有人称还引发了几个月后爆发的社会事件)至于阶级对立分隔、中产阶级的虚伪、移民的融入……这些似乎一直没有最佳解答,在人类社会中永远存在的问题,在不同时期的比例、份量、凸显侧面都很不一样。
影片初放时,我猜自己感兴趣的,是揭露中产嘴脸。
而今,我感兴趣的,是阶级对立的难解与加剧。
所以,结尾处,两人后代在学校门口交流,初放时,我会欣慰于仇恨在第二代消失。
而今,我在想会不会是又一轮阴谋(当然会包装的很温柔)的开始呢?
导演作消音处理,实在太有远见!
他似乎预测了各种不可控制的走向!
自杀段落、干脆利落到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最佳观影地大光明电影院有人发出惊呼,我周边所有观众都和我一样,虎躯一震,倒吸一口冷气,整排椅子都同时震颤了一下,我似乎都能听到,余震在大家心里,久久回荡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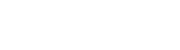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具象版...真的有点无聊对不起
无聊沉闷压抑。童年往事确实有点吓人。So who did it?父子都义正言辞地否定,不得不相信。And what's the point? 好压抑咧。怎么不早点报复,记了这么多年,是有多恨。那段历史是真的不,真是不光彩啊,法兰西。
哈内克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抛弃大部分闲散日常纪录,取其潜意识深处的最惧怕的事,你可以看到那些录像带如何把这个家庭击垮,看到这个人对不同的人千变万化的面孔,以及精神崩溃的一面,电影又抛出了一句话:你真的能问心无愧吗?
自刃封喉喷张的血流,并未清洗往事的清白,反而给彼方挥之不去的黑白梦魇多了一抹更加浑浊的浓稠。片尾的长镜头,台阶上下一代的重逢,是再回首,是泯恩仇,未知可否。
狀態不好的時候看悶片真心折磨,尤其是法語片,於個人。
(4.2/5.0)割喉加重了本片的陈词滥调感——“平静中爆发”的拍法已经看得够多了.
令人难忘的长镜头,那只被割喉的公鸡和自刎的Majid。历史、社会、家庭遗留的触目伤口始终难以愈合,哈内克式惊悚冷冷的很锋利,哪怕是《爱》也时而瘆人
一次坐立不安又酣畅淋漓的奇妙观影体验。
盗版碟
好平淡的镜头,好强大的内容
哈内克,一名坚定的低端人性黑论者与虐观众狂。这种片在所有高端艺术上档次的手法幌子背后本质跟完美陌生人那种所谓高分烧脑片没什么区别。“天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居然如此脆弱/The colonial past still haunts us!” (做惊恐状)FOR FUCK'S SAKE.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是一种平静的恐慌,这部电影很好地呈现了这种恐惧。男主的怯懦和偏见,也令人心寒。电影中涉及的政治元素我不太关注,导演想表达的意思也可以查阅相关解读。最后没有明确指出是谁拍了、寄了录像带,观众自己去猜想,很有意思。第九十分钟,就是刀抹脖子之后,画面中的海报很有意思。电影最后也很有意思。01:57:53,mkv,2.04GB。豆瓣7.6,第16568人评分
我已经看腻了中产阶级这些小破事儿了
喜欢看娱乐片的就不要看了,HANEKE的作品是养活理论界写论文的
汉内克曾说,在原来的剧本中,本来为结尾的这个镜头中准备了长达两页的台词,让新一代的人表达自己的关系。但最后他认为这样的结尾违背了影片的主旨,为此消去了所有的对白。
打开才意识到是以前看过的片子。正如片中那无聊的录像带一样,你也可以选择快进。
我对这部影片的反应恰如其分地映衬出自己浅薄的欣赏水平
是否拍摄的有点太无聊了,以及这个男主让我想起追风筝的人,讨厌的感觉瞬间涌上来
6.6分 很好奇在短评中说“这是对中产阶级最鞭辟入里的描绘”的一群人,你们咋就那么自信地觉得自己最懂中产阶级? 仍然是哈内克冷静克制的调度,只不过看他电影越多越觉得《钢琴教师》的表现力是他自己再无法复制的了;本片不过是杀鸡和割喉两段来到波峰,男主妈妈这角色很有趣,其余基本没什么新东西。 先抛开阶级描绘不谈,我敢说政治隐喻绝不是第一要义,不然只是更加失败。再说回阶级描绘——至少对我而言,我并不能理解人物的行为逻辑。可能我太沉迷上帝视角了,但中产的自私傲慢并不代表脑子一根筋。。 虎头蛇尾的电影;谁送的录像带我不在意,但所有的矛盾都写的太刻意了,又偏偏不精彩也不压抑。 比诺什演的好。
如果不是亲眼看过,很难想象这世界上会有这么无聊的电影。